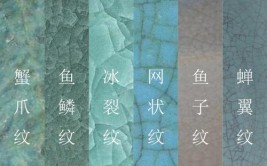田志力小时候,家里常用一件装小菜的豆青釉瓷碟,上面有两个钉痕。据家人说,碟子传了好几辈,虽是摔裂过的小物,但锔补了还能使,便一直用到现在。
五十多年过去,退休后成了一个“修补匠人”的田志力,每次吃饭见到这只碟子总要感慨:自己这种珍惜器物的心态,或许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惜物积福,也是匠人之心啊。”
田志力家中的清晚期豆青釉小碟,碟上可见锔补痕迹

1
大漆大美,找回缺失的记忆
三年前,五十五岁的田志力半路出家,开始了修复器物的生活。
但他的手法不是“锔”,而是以大漆为介质,对陶瓷、紫砂、玉器甚至是竹器、木器进行修复。
锔,是以订书钉一样的方式修补破损器物。这一手法虽牢固,但需钻孔打眼,过程不可逆。与之相比,大漆修复虽然耗时漫长,但对器物没有伤害,修补表面也更为平整。
在日本,用大漆修复并施以金粉或金箔装饰的手法,被称为“金缮”,是非常受尊重的一种工艺技法。
田志力修复的金缮霁蓝瓶
田志力说,国人对“漆”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许多人将“大漆”与日常生活中的油漆、清漆混为一谈,认为其有毒害,是化学物质。
其实,仅仅是观察“漆”字的形态,就能看出其自然属性:左为水,右为上木下水,中间左右各一撇,如同插入树干的竹片,将木中液汁导引而出。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漆,是从漆树韧皮部流出的纯天然浆液,即“大漆”。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漆便被智慧的先民采用。
《说文解字》中说:“桼,木汁,可以髹物。”描绘的正是大漆优质的修复力,而“如胶似漆”一词,也是以其强黏合性形容亲密关系。
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在田志力看来,大漆之所以能被称为“大”,与其本真特性不无关系。大漆纯粹、可再生,还具有防水、耐腐、耐高温的稳定特质,既可涂饰又可塑形,因此,大漆不但无毒,还是修复珍贵器物的优选。
“认为漆有毒,其实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缺失。”田志力说,“找回关于漆的记忆,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2
修复如手术,匠人亦有“仁心”
每天早上,田志力都会一头扎进工作室,一待就是一整天。
一件破损件到了他手中,先要对残断面进行清洗,再用面粉与大漆混合成漆糊,将碎片拼接粘合,荫干后进行修缝、补缺等步骤,需要有修饰效果的,还要对其上金。
田志力修复的建盏
过程听起来并不繁复,但上手操作,却要耗费极大的的心力。比如田志力修缮数目最多的建盏,通常有失釉、开裂、残缺三种状况。失釉,需反复刷漆烤制,揩擦打磨光亮;开裂,则用漆糊黏合;残缺,最为费力,如果情况严重,甚至需要“夹苎”。夹苎,是先按照对器型的揣摩以泥塑型,再以漆灰批刮的苎麻布塑型,干后挖去内里的泥型,脱胎为完整器再髹饰。
田志力曾修复过一只汝窑的香炉。小小一枚三足香炉,摔成两半不说,还缺两足,少一耳。他以仅余的一足一耳为参考,查阅各种材料,才确认其形制,动手进行重塑。整个过程采用“夹苎”的方式,完全靠麻和漆泥进行再造。这场浩大的重建工程,花费了整整一年光阴。
田志力修复的紫砂壶
宋元茶盏口沿漆修,修旧如旧
修复的器物多了,也会遭遇困境。前些日子,朋友送来了一个破烂的竹编小盒,是装建盏的,从日本购得。田志力端详了几天,也没想出好办法:内壁漆层破损的实在厉害,竹坯又极细致精巧,实在无从下手。
他去求助文物修复的老匠人,总算得了一条明路:把漆灌注在注射器里,像打针一样,注入破损的竹缝间。如今,田志力的工作台上常放着几只注射针头,这让他更为真切地感受到,文物修复者,的确很像医生,需要有精湛的技艺、极大的耐性,更要有对残损器物极大的热爱和珍视。所谓“医者仁心”,修复匠人所保有的,也正是这样一颗对器物的仁爱之心。
3
以器载道,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因为经常要还原残损器物的样貌,田志力开始了对器型的探索和研究。
吴山的《中国历代器皿造型》,他经常翻阅,越是看,越是惊叹,“中国的器型,太丰富了,太惊人了。”
由此,他进一步探究中国人“道”和“器”的观念,试图从器物中认知传统文化。他读《周易》,得知“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又读《考工记》,了解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因此,田志力体会到,匠人制器,还是要讲究“以器载道”,通过器的形态、技术、手艺,来传达审美、格调、价值,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道。”
田志力创作的脱胎朱髹葵口盘,此为宋代器型
因此,无论是做修复,还是搞创作,田志力都注重对古代形制的继承,不随意臆造,不“离经叛道”。“拿盘口来说,五瓣梅花是宋人的风格;金边菱花口,是唐代风尚,”田志力说,“这些本质上都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形态的一种传达。”
另一种传承,在简素的品格上。“我们现在喜欢宋人的生活、明代的家具,其实都是对至简生活的一种回归,”田志力说,“而大漆,恰恰符合这种至纯至简的品格。”
田志力创作的脱胎素髹折沿菱花口盘,这也是制作难度最大的器物之一
因此,他做的漆器,以黑色为多。比如那只耗时一年才修补好的汝窑香炉,田志力坚持没有上金,而是对修补处留存了黑色,做了哑光处理。
修复最终完成时,朋友都被香炉所呈现出的朴拙、大气所震撼。“庄子对美的看法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田志力说,“古人简素的美学观,世代传承而不过时,而器物的朴素之美,历经千年依旧动人心魄。”
4
惜物积福,以工匠精神守护心安之处
三年间,田志力免费修复的器物有近千件,多来自喜好收藏的朋友,其中有珍贵的建盏、汝窑,也有日常用的紫砂小壶,用了多年的茶盘。
在田志力眼里,每一次相遇,都是难得的机缘。越是残破的东西,越不容易假,越是有古意。而在修缮的时光里,时刻都能对着有上千年生命的器物认真端详,将其捧于手中细细摩挲,如同与历史进行一场悠长而深入的对谈。
而那些日常使用的器物,有些并不金贵,但因为友人长久的使用与相伴,也便有了温度。 “越是我们经年使用的,越是希望它陪我们更久。”田志力说,每一次修复,都是一种温度的叠加,“把我对器物的珍视、对友谊的珍视,也都倾注其中了。”
田志力为友人金缮的名家瓷杯
朋友使用多年的紫砂杯,经田志力金缮后重焕生机
物质的富足,让人们逐渐忘记“修补”的概念,需求转为欲求,脆弱的器物一旦破损,便遭丢弃。在田志力眼里,这种生活粗糙而缺少品质,他更喜欢“侘寂”的生活美学,这是一种日本式的精神向往,是一种对待不完美的生活智慧。
田志力说,匠人修复器物,就是对侘寂美学的呈现。它不刻意突出装饰和外表,相信无常之中有美,对不完美事物全心接纳与宽恕。修复,是对随机、不对称和转瞬即逝的美的崇尚,让自己爱上脆弱的事物,也宽容同样脆弱的内心。
修复中,匠人的用心付出与对物出自同理心的关怀,放大了对生命的感受,对万事万物更为珍惜。这种技艺,是人与物的连结,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
这个五十五岁才开始学漆的人,对于修复之道有着更深刻的体悟。“之前我从商,学的都是谋生的手段,现在学了手艺,才知道手艺比手段高明无数倍,”田志力说,“修复这门手艺,是一种精神上的修为,更是一种内心的安放。”
田志力(右三)为大漆爱好者免费授课
在田志力眼里,每一件承载着时光、带着温度与情感的器物,都是心安之处,如同家里那只豆青釉的小菜碟子,传递着一个家族的温情,寄托着祖祖辈辈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安放着一颗惜物爱物的匠人之心。
马益群
资深收藏版编辑,中国副刊品藏栏目主持人。亲历了中国收藏界和艺术品市场兴起发展的整个过程。雅好收藏,偏喜奇石、紫砂壶。出版专著《大漠奇石》。现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奇石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编:周玉娴 |编辑:袁浩
—END—
匠人亦有“仁心”
热门阅读文章
★ 本号姓“副” 欢迎来“刊”★ 王蒙:不忘金庸★ 大地有多大★ 王钢:忍别二月河★ 三会大侠——追忆金庸先生★ 花甲副刊“朝花”,人间哀乐关情★ 追忆与漫画大师方成的“忘年交”★ 毛泽东呼吁请保留专刊副刊★ 1979年的那个春节★ ”北京老壶”的壶中天地★ 有一种乡愁叫小名
长按二维码关注“中国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