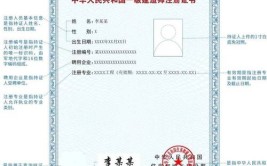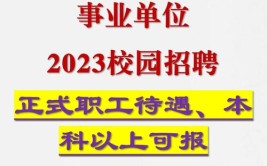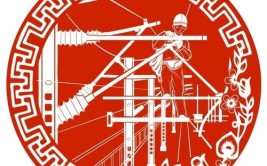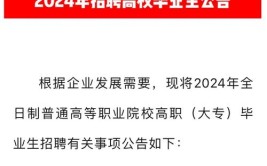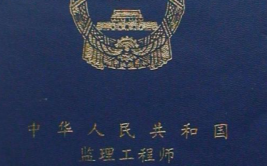对于长北以外的山西人来说,铁三局一处是个熟悉而陌生的企业。
说陌生,是由于铁三局一处地处长北,和长北众多厂矿企业和家属区连在一起,外人很难把彼此间的生活区和办公区区分开来,在方位上常常把与之相连的郑局长北铁路段、太锯等大小单位混淆;说熟悉,由于九十年代在长治时常可以看到铁三局一处的企业文化和相关广告宣传,铁三局水泥厂、铁三局三长沙发厂这些单位的广告在那个时期频繁现于报纸、电视甚至田间地头和厂矿企业的墙壁上。
河南郑铁路局长北段、东北过来的铁三局一处、天津内迁的太行锯条厂这是原长北街道办事处驻地所在的长北核心区域人数最多的三大厂矿,剩下的就是长治幼儿师范学校了。

随着亚洲锯王太行锯条厂的没落,大部分天津人离开了长北回到津门;郑州铁路局长北段的缩编,河南人从长北分散到南太焦沿途;铁三局一处再屡次整编改组,落户于天津成为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的一部分;长治幼师撤并升格为长治幼儿高等师范学校之后,也离开长北迁往主城新区。最后,日益萧条的结果导致长北街道办事处也被撤销建制与马厂乡镇合并,使长北这个行政名称彻底消失,从城市街道驻地转变为一个乡镇中心。
走的走、撤的撤、并的并,留下了一个寂寞的长北,只有那些大小单位在用的、空置的办公楼和家属区见证长北曾经的喧嚣与辉煌。
从长北消亡的这些企事业单位,无疑数铁三局一处走的最彻底。不仅与驻扎在太原的老东家铁三局割舍了两者原有的隶属关系,还离开了山西辗转到天津成为中铁旗下新方阵北京工程局的一员。
去黄碾,走榆黄路路过张庄,一哥们指着马路东面铁路那边一大片高矮参错的区域说那是铁三局一处,并连说可惜了。我笑问他怎么可惜了。
我虽然不知道铁三局一处到底在长北哪一片,可我知道这个单位的发展现状在长北曾经众多的企业中还算是不错的。
哥们说的可惜就是指倒闭了。
看来这哥们知道铁三局一处,但却不了解这个单位的来龙去脉。
铁三局源于东北林区铁路建设,起源于铁道部内蒙库图段。
从1952年的库图铁路工程处到1968年6月铁道部第三工程局这个名称定型出现,经过八次整合,经历了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牙克石工程分局、铁道部新建工程总局第七工程局、铁道部东北森林工程处等名称变迁。
而铁三局一处则成立于1959年4月,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修建晋北宁武到岢岚的3201铁路,从黑龙江、吉林来到山西。
在1979年3201铁路竣工后,又随着铁三局对太焦铁路建设的全面接管与承建,从晋北迁入长治施工。在完成太焦铁路和长邯铁路的建设后,在铁三局常驻太原布局华北,长北也渐成为三局一处的机关驻地。
2000年5月铁三局一处更名为铁科公司,铁科公司由铁三局、国铁研究院、铁一勘设院、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一工程处和兰州铁一院共同组建。
在更名两年后2002年底又改为中铁三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期期间,随着中铁三局在华北项目的增多,长治人口中的三局一处开始启动了机关往河北霸州市的搬迁。
霸州,是三局一处在承建京九铁路标段时候的一个重要项目基地。在2000年后,河北霸州的地名中多了一个叫铁三局一处的地方,而长北原一处的大本营则成为长北基地,生活着几千户离退休职工和家属。
在迁入河北霸州九年的后的2010年,在中铁“推进两大转变,实现二次创业”的重大部署下,铁三局一处又与铁一 局一处、铁建北京分公司、华润划过来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重组整合为中铁航空港集团,并在2011年成为中铁航空港集团第三工程公司,落户于天津虹桥区。2017年底,随着中铁航空港集团名称变更,又改称为中铁北京工程局天津分公司并延续到现在。
作为一个职工与家属人口在最多时候达到上万人的央企,三局一处在成建制转隶的同时,一处旗下的工程队和项目部,几十年间在铁三局系统内外也时有调整,最早的涉及人数多的就是华海公司了。
1985年,“立足三晋,开拓沿海;修路为主,多种经营”,成为时为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的发展方针,地处长北的三局一处在上海籍的处长带领下,组建了上海工程队,拿下石洞口电厂建设,首次跻身上海市场。在七年后的1992年,铁三局将一处的上海工程队与后来进入上海地铁施工的五处11队和市政施工的二处桥梁、构件厂,整合为直接隶属于铁三局的华海工程公司。而华海工程公司在2010年在中铁总公司层面的战略重组下,为解决中铁在上海没有二级公司的问题,与中铁上海分公司、中铁四局六公司、市政公司合并为现在的中铁上海工程局。
在2012年,时为中铁航空港三公司的一处,旗下的长沙项目、杭州项目、重庆项目,按区域被重组整合为为中铁航空港二公司、杭州分公司、重庆分公司,后来分别改编为中铁北京工程局二分公司、九分公司。重庆分公司在改名为四公司后,又易名中铁北京工程局城轨公司,搬迁到安徽合肥。
随着部分项目部与施工队的划出重组,原三局一处在册的三千多人,也减少为千余人。这千余人构成了今天的中铁北京工程局天津分公司的主体。
这些分布在北京、天津、长沙、杭州与合肥的原铁三局一处的职工们,如同他们早先随着修铁路来到山西的老一辈一样,人随项目走,跟着新的项目项目也随着新的分公司继续奔赴在新不同的省份与城市间。与老一辈不一样的是,身在他乡的他们已从最初东北人的称呼转变为山西人,历史也变为从山西过来的老一处,在几代人的传承中,地域标签都有了新变化,从白山黑水的东北变为表里山河的山西。
在长北,铁三局原来有铁三局一处、铁三局电务公司、铁三局六处的潞城汽车三分队,由于历史欠账多,成为长治老国企棚户区集中的地方之一。在一处归于中铁航空港之处,中铁航空港启动了小辛庄家属区的棚户区改造。如今长北老铁三局一处家属区三供一业和原来的学校、医院都移交给地方,只有那原一处机关、铁三局水泥厂、铁三局一处综合厂等资产和四千多户家属由中铁北京工程局长治事业中心和中铁宏达运营管理。
在“低头拉车不看路”的历史欠账下,如今铁三局一处家属区虽然在棚改后有的片区面目焕然一新,但是整体上依然与长治主城区有着强烈的反差。随着主体单位的搬迁离开的时间增长,没有新的增长活力注入之后,在多数职工子女升学、就业的相继离开,这些老家属区就有了一种萧条。
这种萧条,如同曲终人散后的落寂,也犹如潮水退却后的平静,让曾经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徘徊而怀念,最终流落成为他乡让这里成为所谓的根,而根又容易被岁月忽视,树高千尺最不起眼的就是根。
相对于被撤销街道办事处长北的今天,计划经济时期是长北最沸腾的时光。那个时候长北的繁华,更多的是来自众多企业先后落地带来人口的输入,如同潮涌支撑起长北的发展,使长北成为长治的副城和襄垣、郊区、潞城的中心。
从长北街办到马厂乡镇,从城到镇,这是从城市的量体发展到乡镇中心的萎缩,这种萎缩背后就是就是一座座企业的消亡离开和与之相随的人口流出。在现实中,这种撤并更多的是在行政上打破历史上均衡的南北规划布局使之倾斜,来成全和间接服务新时期长治主城区的扩张需求。
无论是今天的长北还是过去的铁三局一处,面对未来,对过去来说是个没有终结开始;面对过去,对现在来说又是个重新开始的过去。
这对于老三局一处基地,还是中铁北京工程局天津分公司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