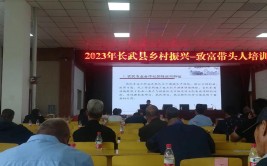月光、灶火和呼嗒呼嗒的风箱声,30年过去了,仍清晰地影印在我的心幕上,流淌在我的血流里,响彻在我身前身后的空气中。
那是30年前的中牟的白沙。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我从郑州回老家杞县接母亲来郑州定居,顺便把给在家中做事的弟弟买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骑回去。

上午8点出发,按正常情况骑下来,8个小时后我可以回到杞县县城,加上中途吃饭、休息的时间,该是下午6点的时候。从杞县西关骑到县城中心的城隍庙喝碗杂烩汤,然后趁月色走18里路回到村里,大体应该能在晚上9点之前赶到。
谁知,刚出郑州,行进到白沙村口,车子坏在那里了,飞轮出了问题。师傅说马上修,但飞轮得去中牟县城买,这么一折腾,就到了傍晚。
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赶在西边的太阳还没完全沉入地下之时,就从白沙村东的屋脊上升起来,把屋脊两端的翘首兽头照成了黛色的剪影,镶嵌在流光漂浮的天幕上。
那时的我还很年轻,虽然还没达到随遇而安的修为,但有的是随遇而安的不得已与可摔可打的身体。于是,从修车铺推上刚换上新飞轮的“飞鸽”就住进了附近的车马店。
白沙的傍晚和当时诸多的乡村一样,静,但声息却很丰富、温暖。一阵吆喝着老牛犟驴回家的声响之后,满街都是“呼嗒、呼嗒”的风箱声。
炊烟弥散在夜色里,更给摇动在树梢上的月光增添了几分朦胧。随着夜色的加重,风箱的呼嗒声渐渐沉寂下去,街头东一声西一嗓呼喝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唤声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响起来。粗门大嗓的喊声往往比较急促,在外玩耍的孩子应答也往往较快较顺从的样子;细声细气的呼喊往往会把声音拖得细长细长,像似要把村中曲里拐弯的胡同游走一遍似的,而孩子的呼应也往往较为迟缓。
听到别人家吃饭的声息,我的肚子也“咕咕”叫起来,于是就走到车马店的门房那里问掌柜的有什么吃食。
掌柜的很客气,反复解释说这是小地方,庄户人都自己回家做饭,没饭店。掌柜的看我听了他的话有些失望的样子,于是又说,“我这门房有个火炉,是为客官烧开水的,要是你带了干粮,我这有锅,也可以帮你烩烩,掌盐不要钱。”我没带干粮,谢绝了掌柜的好意。
看着我饥肠辘辘的样子,掌柜的像欠了我二升高粱米一样,扎煞着手,不知怎么样才好。转而,他有点兴奋起来,出得门房扯着我的手到车马店大门口,向东一指说,“东边路北有家蒸馍铺,你可以去看看今晚的馍出锅了没有,就在东边响着风箱的地方。”听了掌柜的话,放眼东天月光曼妙的村子,我的耳际真的响起了“呼嗒、呼嗒”的风箱声。刚才肚子饿,对吃食的向往盖过了以上所有的声响与风景。
打量着月光下紧闭的庄户人家的院门,踩着高一声低一声“呼嗒、呼嗒”风箱耳板的节奏,我高一脚低一脚向村东摸索。
静寂的街道显得格外空旷,村东风箱的呼嗒声显得遥远而又膨胀,似村庄的呼吸,张弛间饱满着生活的温情。路边高树枝头鸟巢里,偶然间会传出梦醒时飞鸟扑打翅膀的扑拉声,如鱼跃于湖面,夜空中荡漾着声波惊起的月光涟漪,悄无声息地氤氲波动。
不知从何处传出的稚童惊夜的哭叫,会突然把夜色撕裂一道口子,随着那哭叫的戛然而止,裂口又会迅即弥合。村东不紧不慢的风箱的呼嗒声时起时伏,不断地以自己的节奏归整着村庄夜色的秩序,也牵引着我那饥渴的脚步,来到当时的白沙村唯一的蒸馍铺。
铺面很小,就是一间临街的门面房。房子临街的一面没有传统房子或砖或土的墙壁和屋门,整个前门脸全是用厢板扣成。
这种用厢板扣成的“门墙”,过去许多村镇集市的生意铺子都这样。这种门墙合一的厢板门面,其实很能彰显我国古人建筑智慧和生意人的精明。一面墙全上了厢板,墙立门关;卸下两扇厢板,门就开了;把全部厢板卸下来,整个铺面就展现在顾客面前,不仅铺面敞亮,也方便顾客挑选商品。
另外,我国城镇商铺门面商品摆放以及空间使用也是有讲究的。比方,货摆明处,这不仅仅是为了使顾客能看清物品便于挑选,同时也表明商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一切全是摆在那“明摆着”的真实。为了追求这个“明摆着”的真实,传统乡镇饭铺的“汤锅”或“馍锅”往往就垒在门面房一侧可以让过路客人一眼就可望见的地方。这样,汤锅馍笼的热气自然就成了主题鲜明招人眼光诱人口水的招幌。
白沙的这间蒸馍铺也是这样,蒸馍锅灶就垒在门口面对大街。灶膛里缠绕着奔突着的火舌与笼上的一团团蒸汽搅拢来又弥散去,飘进夜色溶入月光,有些个玄妙神秘。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时候,幸福降临得太快、太突然、太让人猝不及防。
当我刚走到蒸馍铺门口时,在“嗨”一声吼喝下,那笼热气腾腾的蒸馍出锅了。不由分说,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毛钱半斤粮票递给蒸馍铺的老板,老板看我空着手什么东西也没带,就抽根筷笼子的竹签子串起两个热腾腾的白馍递给我,顺手又找给我两分零钱,说:“等等,我去柜上给你找一两粮票。”我一手擎着用竹签串起的两个白馍,一边无所事事地站在门口。老板在黝黑黝黑的柜橱里翻腾了一阵子,扎煞着两只空手对我说,怎么都找不到一两的粮票了。说这话时,我看到了他的一脸无奈。我说那就不用找了,转身就要离去。这时,老板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边说让我再等等,一边又转身回到他的柜台后,嘴里还反复念叨着:“我咋能沾你这个光呢!
我咋能沾你这个光呢!
”弯腰从柜台后捧起一捧什么走到我面前说:粮票就不找了,送你一把花生就馍吃吧。这时的我,真的一下子被老板的这一举动感动了,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做点什么,一任老板把那一捧花生装到我的衣袋里。
那天,我回到车马店,喝着车马店老板用大铁壶提来的热水,就着花生仁吃完那用竹签串起的两个大白馍,闻着仍有阳光味道的大通铺上稻草的香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而这一梦,就已过了30年的光阴,我再也走不出白沙那个夜晚清凉的月光,再也走不出大白馍就着花生仁的香甜,再也走不出万物皆有声的静寂,再也走不出那一壶开水和一把花生的乡亲温情。真的,一个晚上的时光对于人生来说是短暂的,但一个晚上的味道直直浸染了你的一生,的确也够得上说悠长。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人来人往万事悠悠,试想,有几件事几个人能深埋在你的心底,镌刻在你的记忆深处呢?说真的,白沙的那个晚上无论是就这个村镇而言还是就我这个人而言,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就这个村子而言,无非是和其他所有村子一样,拥有漫天月光,一帘静谧,万籁俱寂;对我而言,也不过是羁旅客店,两个白馍,一捧花生。但那个晚上又为什么能让我永生难忘呢?在我后来多次来去白沙的时光流逝中,才渐渐清晰了白沙的这个晚上深深印在心底的原因。
在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还曾多次到过白沙,也曾多次从同事朋友嘴里听到过白沙。
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回杞县老家,此时正值白沙大集,街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城里人常见的小商品;两厢的商店大多做了花花绿绿喷绘门面;村头的车马店好像已换成了贴了白瓷片墙的三层小楼,经营的好像还是旅馆的生意。
村东的蒸馍铺早不知哪里去了,一家挨一家的饭店的大门上大多写着内设“雅座、包间、野味、炒菜、扣碗”等字样。街边的小摊上大多安放着高音喇叭,高声叫卖着自家的商品。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和过路汽车喇叭的尖叫纠缠在一起,形成分不清节奏主次的共鸣。
白沙变了,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变得充实而又热情奔放,变得饱满而又鲜活,变得繁荣而生机勃勃。
在此之后的一个夏日夜晚,我和几个友人也曾开车到过白沙,那次是专门到白沙来吃烧烤,满满一条大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商铺门头的霓虹灯交相辉映。这自然会让我想起当年骑自行车羁留白沙的那个晚上,心想,如果当年也有这么多吃食,这么热闹,我的那个晚上也就不会那么冷清了。
后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到白沙的时候越来越多起来,去的因由也多种多样,比如去那里给自己的爱车更换一些证件,去那里的建筑材料市场买一些室内装修材料,去那里附近绿博园游览消费,去那里的方特游艺中心游玩,去那里的楼盘看房子,去那里的某个酒店参加文友的笔会,等等。
再后来,各种媒体关于白沙的重大消息也越来越多起来,比如郑州几十家省直单位将迁白沙,阿里、百度、腾讯等一大波互联网企业要在白沙组团集聚,白沙要建大数据产业园,等等。
白沙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离我们理想化的现代城越来越近。直到近来,白沙被从中牟县直接剥离,划归郑州市郑东新区直接管辖。
昔日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的白沙镇变成了今日越来越国际范儿的商贸城;昔日那个低低矮矮的白沙,现在是真的高高大大起来;昔日那个冷冷清清的白沙,今日热热闹闹、火爆了起来;昔日那个传统土气的白沙,现在绝对现代时尚起来。白沙,彻底变了,我记忆中的白沙,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心中,突然泛起一漪五味杂陈的感觉。白沙的发展变化的确如我们国家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一样让人心生喜悦,让人感到莫名的振奋。但是,沉静下来,我还是难掩心中的丝丝忧虑,感伤那个静谧月夜中波动着尘世间温情的小村的逝去。
真的,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也不缺少对现代文明的真切向往。我知道历史与文明总是要进步的,且任谁也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我知道白沙这个地名原本就不存在,站在现在的白沙西望,是过去的圃田泽,这里也曾是渔歌菱唱,舟楫帆影。历史与自然的步伐把圃田泽走没了,泽枯地出,沙粒如银,人们在这银沙滩上盖起了房子,种植了庄稼,才有了如今的白沙。
站在如今的白沙东望,是一代枭雄曹操驰骋疆场,成就一代霸业的古战场官渡,如今的官渡早已不闻古之英雄奔突冲杀马蹄的鼓音,连一点古战场的陈迹都不见了,就连在此之北300里处漳河岸边的魏王西陵,也难辨真假。
历史毕竟不是向后走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春去秋来,沧海桑田,这本来就是历史的自然。一个仅只让我住过一晚的白沙的变化,又何致使我忧伤难抑呢?况且,如果让我回到那个住车马店的贫穷年代,也是我绝对不愿意的。那么,面对这个物质世界巨大丰富的今天,面对这个变得富饶、现代、时尚的白沙镇,我又为何忧虑感伤呢?对此,我真的问询过历史文化,问询过我记忆的历程,问询过我的良心和良知。
我曾遥望星空问询过浩瀚的宇宙,也曾站在山头问询过高山、大川、江河和湖泊,问询过飞鸟和树丛中的刺猬,问询过花朵和落叶,问询过风霜雾雪,问询过我经验的现实和梦想,我才清楚,在我们不缺吃穿、不缺住房和饭店,不缺汽车和高速公路的今天,我的白沙所缺的却是那曾浸染过我心肺的银沙一样的月光,缺少那红砂糖一般甜蜜的母亲呼唤儿女回家吃饭的歌吟,缺少的是人回家、畜入圈、鸟归巢的那份自然安适,缺少的是天涯若比邻般的乡亲的温馨。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省著名诗人苏金伞先生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寻找》。诗作抒写诗人回到开封寻找他的童年记忆,寻找他上大学的讲义,寻找杨家湖边曾见证过他的爱情热吻的岸柳以及他住过的监狱的心情。
诗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对开封我怕弄得面貌全非,致使我回去难以认识;但又怕面目不变,老友凋谢而城郭如昔。”苏老的诗情真意切地道出了我对我曾住过的白沙,准确地讲是我对我脚下的这块土地,在历史的进程中变与不变的悖论式向往。
在此基础上,我还想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努力消除了贫穷而导致了自然与乡情的贫困,这则是我们所不乐意看到的。
白沙,白沙,我的白沙,我不想失去你给我留下的记忆的美好,也不想让你丧失发展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