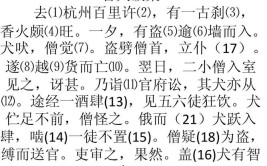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位高僧身边,往往聚集着一群士大夫。这种现象从东晋时期就表现得很突出,随便翻一翻当时的史籍,便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文/周濮
两晋之际的高僧康僧渊,本是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和殷浩辩论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和康僧渊一同渡江南下的康法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出《高僧传·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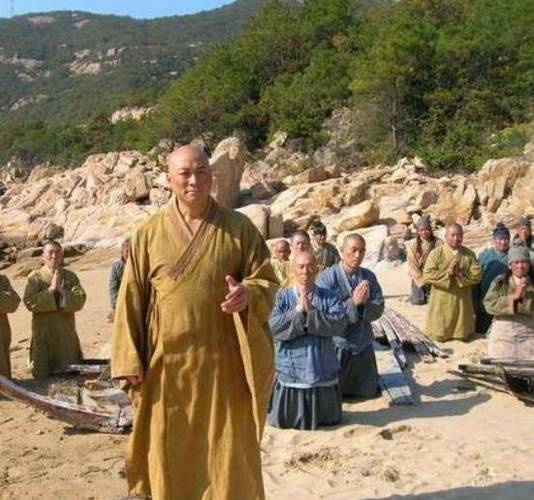
支道林,名遁,世称“支公”,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几乎可以说是生活在当时的士族精英中间,和他交往过的名士有王羲之、谢安、谢玄、许询、孙绰、王修等。
道安大师与学者习凿齿有着密切的往来,二人初次相见时,“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的妙对,为世人津津乐道。前秦国主苻坚攻陷襄阳,将道安大师和习凿齿接往长安,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高僧传·卷五》)因为习凿齿有脚疾,所以被戏称为“半人”。后来道安大师规范整顿佛教,习凿齿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莲宗初祖慧远大师身边,有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名贤隐士,另与陶渊明、谢灵运、殷仲堪、桓玄等人也有交往。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伴随着佛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而出现的。
01
佛理玄风,缔结胜缘
魏晋时期是高扬出世精神的时代,士人学者虽然是世间之人,但在当时却又有着明显的出世情怀。他们作为士族子弟,莫不传承家学,或儒或道,各有所专。而在家学之外,则诸子百家、方伎数术,无不涉猎。
老庄之学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备受青睐,文人雅士崇尚清谈,玄学之风大盛。这一时期,佛家般若学派出现繁盛局面,僧人们又长于谈空说无,发挥妙理。因此,当梵僧陆续来到中国之时,“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钱穆《国史大纲》),佛法中般若空性的学问,也以儒、道格义的形式呈现于世。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将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的中国佛教称为“士大夫佛教”,认为当时的僧人就是“披着袈裟的士大夫”。因为那些僧人虽然是方外之人,但也是通晓世间各种学问的博学之士。
《高僧传》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僧人:鸠摩罗什“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竺法潜“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史宗“善谈《庄》《老》,究明《论》《孝》,而韬光隐迹,世莫之知”;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释道融儿时读《论语》,过目成诵,到而立之年,“内外经书,谙游心府”;释僧瑾“少善《庄》《老》及《诗》《礼》”;释法瑗“论议之隙,时谈《孝经》《丧服》”,等等。
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推重僧人的操履德行,把“天竺七僧”和“竹林七贤”相比况,可以说是当时主流士族阶层对佛法的认可和接纳的佐证。(《道贤论》现已不存,内容散见于《高僧传》:“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竺法)护匹山巨源。”“以(帛)法祖匹嵇康。”“以(竺法)乘比王濬冲。”“以(竺法)深比刘伯伦。”“以(支)遁方向子期。”“以(于法兰)比阮嗣宗。”“以(于道)邃比阮咸。”)
东晋世家大族子弟出家的现象也时有之。琅琊王氏家族中,大将军王敦的弟弟出家,为竺道潜。宰相王导的弟弟出家,为释道宝。这种世家子弟出家的情况,在后世也屡见不鲜。唐朝宰相裴休,出身河东裴氏,世家大族。宣宗帝常对人讲:“休,真儒者也。”他的儿子裴文德虽然中了状元,但是裴休作为父亲,最终的选择却是送儿子出家。他在《示子出家偈》中殷切嘱咐:“含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身眼莫随财色转,道心须向岁寒存。看经念佛依师教,苦志明心报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间天上独称尊。”出家为僧,荷担如来大法,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唐朝的宰相杜黄裳,在临终的时候遗憾自己一辈子无缘出家为僧,遗命嘱人帮他剃染之后再入殓。宋代也有名相王旦,遗命亦然。
02
僧士交往,世代相传
僧人们的道德学问为世人所敬仰,成为引领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钱穆先生说:“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国一些大和尚高僧们。我只拿一个普通的人格标准来看和尚高僧,来看他们的表现。但中国高僧们,很少写进《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人物实在太多,《二十四史》写不尽。”(《国史新论》)
僧人与士大夫的交往,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历代高僧的行迹,及其与士大夫的交往,有很多很多。但在正史中,有很多内容被剪除了,就像印光大师所说:“《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在现存的典籍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幸读到很多僧士交往的动人故事。
唐朝的时候,白居易笃信佛教,乐于亲近寺院僧人。他亲近鸟窠禅师,鸟窠禅师为他开示佛法要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在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时候,白居易经常到东林寺拜访僧人。宋朝的时候,苏东坡和佛印禅师关系密切,他们交往的各种趣闻轶事不胜枚举,“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的典故早已广为人知。
而喜欢写艳词的黄庭坚和喜爱画马的李伯时,同时受到圆通秀禅师的点化,因为惧于堕入三恶道,李不再画马,黄不再写艳词。莲宗七祖省常大师在北宋的时候于西湖边结净行社,专门招请文人士大夫入社念佛。到了明朝,蕅益大师则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关系密切。民国时期,印光大师身边有许止净、张云雷、丁福保、高鹤年等著名的居士,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弘一大师身边则有夏丏尊、丰子恺等名士追随。丰子恺虽未出家,但一直对弘一大师执弟子礼,他创作《护生画集》,就是受到弘一大师的影响。
03
内外相资,弘法护教
在佛法初传的魏晋之际,僧人群体能够和本土的文人逸士建立密切联系,正是基于他们知识精英的共同属性以及共具的出世情怀。而在此后大乘佛法深深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僧人无论是译经还是弘法,都得到了这些在家知识精英的大力协助与护持。
在佛法的弘传中,出家人是内护,在家人是外护。印光大师说:“昔如来将入涅槃,以其法道,付嘱国王大臣,令其护持流通。良以僧众舍俗出家,精修梵行。既乏资财,又无权势。纵能宏扬法化,难免外侮侵陵。若得王臣护持,则法化广被,外侮不生。以其强暴横逆者,息影而匿迹。调柔良善者,起信而投诚。故得大张教网,捞摝苦海之鱼。丕振宗风,彻见自心之月。内护外护,相需而行。则如来法化,自可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普令含识,同沐法泽。”(《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
佛法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士大夫可谓功不可没。西晋时期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在翻译经典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得力助手是当时的才俊之士,比如聂承远、聂道真父子,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唐朝的时候,般剌密谛尊者翻译《楞严经》,宰相房融就是其中重要的成员,担任笔受。
由于佛法是从异域传来,难信难解,因而受到过很多攻讦。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士大夫担起了护法的职责,由此诞生了很多精彩的护教文字,比如梁代僧祐律师编的《弘明集》,唐代道宣律师编的《广弘明集》,等等。这些集子里所收录的文章,有很多是当时的士大夫所写,如《弘明集》中牟融写的《理惑论》,宗炳(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写的《明佛论》等。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僧士交往的痕迹。到了北宋,宰相张商英专门写过《护法论》,明朝开国重臣宋濂还著有《护法录》。这类护教雄文,条分缕析的说理,通达无碍的文采,让人叹为观止。
儒家讲“天下观”,而佛家讲“法界观”。在僧士交往的双向互动中,僧人受到士大夫的重要影响,但士大夫受僧人的影响更大。佛法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士大夫的境界。印光大师说过,古来凡是建立不朽功勋的人物,多是由学佛得力而来。北宋宰相文彦博,曾和净严法师集合十万人,举行净土法会,发愿求生西方。这种普愿众生皆得解脱的本怀,已经远远超越了士大夫对“立德、立功、立言”的期许。
0 4
结语
作为世间与出世间的重要角色,僧士交往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倓虚法师说过,和尚是世界的大轴,是维系人心、社会化导的中枢,和尚不能动。僧人以身垂范的大乘菩萨道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资相长,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共同描绘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文章来源丨《净土》2022年第1期
图片来源丨十愿网
摄影丨重影、妙传、丹珍旺姆、孟和德力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