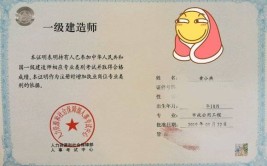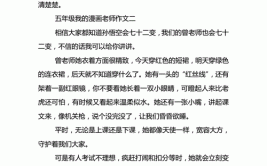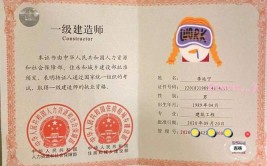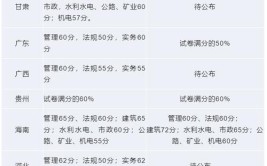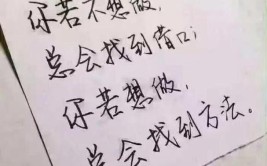查阅古代引泾资料,可以看到引泾工程许多主持人、提出者或是倡导人的姓名,从古到今,林林总总,星光灿烂。如秦时郑国、吕不韦,汉时白公、倪宽,北魏符坚,西魏贺兰祥,唐代公孙无忌、刘仁师。宋元明清资料较多,史实保存较为完整,更加是群星罗列,举不胜举。他们大多是当朝重臣或者本身就是皇帝,侧身于其中者,只有宋代杜思渊身份不详,然而从其上书自称“臣”可以看出,大约也不是个白身吧。最起码也应该是有身份的士人,或者是有名气的地方士绅。可是具体参与工程建设的水利技术人员,或者在施工过程中提出可行性建议的工匠们,却没有一个留在史志中。就是工程出、捐资人的名姓也很难从史料中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遗憾。数以万计的工程建设者,在史志中也只留下了一、两个字,“利夫”、“夫”或是“民夫”就是他们的全部。同样在现代引泾工程泾惠渠的工程建设中,我们也只记得李仪祉这个倡导者、设计者和领导者,诸如华洋义赈会的塔德、安立森等人,还有中方的其它技术人员,如胡步川、刘钟瑞等人,除名字之外则很难再发现更多的资料。
泾惠渠朱子桥
对古代引泾工程史的研究,如果能将当时工程技术资料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保存一点,也不至于让后世的水利研究者白头搔短,苦不堪言了;如果能将当时参与的绅士名姓罗列,捐资金款项保留,则无疑对地方经济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惜,在现存引泾史志中我们只能看到夸夸其谈的儒生与高高在上的官员。话题扯得有些远了,今天想说说参与引泾工程的石匠,之所以能有石匠一点零星的资料,那是因为儒生或是官员在向上级抱怨工程难度很大,或是官员向上级要求追加投资的报告中有所显示。另外那就是耸立在引泾古石渠旁,左侧山崖上孤零零的石匠坟。那些石匠姓氏名谁,没有人知道,没有墓碑,也没有高大的坟茔,那片土地上仅有一堆石,由于当地人口口相传那是引泾石匠的墓地,我们才知道他们这一群体的存在。这里到底埋有多少名石匠,也没有人知道,十分可能也就是一个乱葬山岗而已。

从现存资料至少可以知道,秦代郑国了工没有大量使用石匠,毕竟那时工程位于川原河湾地带;汉代白公也没有使用石匠的记录,虽然对白渠引泾渠口还现在存在争议,但它还是没有伸入山区地带;准确地说在符坚才开始使用石匠,据史载那时“凿山起堤”,役使大姓僮仆和当地百姓三万余人,可能由于施工时间不长吧,再说前秦也只是一个短命王朝,史志中连工程记录也没有保留,从头到尾,仅有几十字,自然是舍不得给那些低贱的石匠了,工程的难度应该不大,毕竟那也就是在山脚,多为卵石和砂岩,比较容易吧。
元王御史渠鹿巷
到了唐代三白渠时期,应该使用了大量的石匠,因为他们在河中有宏伟的石坝,虽然石坝是以数十上百的石堆垒成,如史书记载“河中旧有石堰,修广皆百步,捍水雄壮,谓之将军翣”,很可惜还是没有使用石匠的记录;宋代丰利渠建设时,开凿了石渠,张家山石质刚硬,当时凿石以立方尺计工,石渠截面为梯形,上底宽14尺,下底宽12尺,高深则因地形,最深者达38尺,长度为3141尺,共计有490866日工,在那时以斧凿加以火烧、醋沃的原始方式进行施工,可见难度之大。那么大规模的施工,竟连使用石匠的数量也没有留下,至于在施工过程中死亡石匠的数目也从来没有人说过;史籍上有明确数量记载的是在元代,当年修凿王御史渠,工程倡议者王琚向朝庭建议提到:“计用石十二万七千五百尺,人日采石积方一尺,工价二两五钱,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用火焚水淬,日可凿石五百尺,官给其粮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雇匠,庸值使水户均出,陕西省议计所用钱粮不及二年之费,可谓一劳永逸。”(乾隆年《泾阳县志》)当然后來由于工程量增加,又增加石匠一百多人(见同文)。
泾惠渠大坝(现代)
这段资料涉及到了使用石匠的数量为200人,工价白银二两五钱。雇佣石工匠的报酬在当时受益农户进行筹措,即由灌区所有利户承担修筑耗费的钱粮。唯一让人不理解的是每名石工每二两五钱的工钱,不知编写史志的人从那里得到这些数据,依照常识那也太不可思议了,仅工匠每天开支白银500两,以其所言工程量大约需255日,仅石匠开支127500两白银,这不可能。但唯一可信的是当时石匠佣资应该不低,当地现在还有“斗渣斗钱”的传说,至于真正的工值,则没有具体的数值。
到了明代,相关资料就多了起来,渠首明代渠碑记载则有主政者、组织者和工程实施的过程,从提议到完工,以及施工过程,甚至是文人的赞美都有记录,石碑后面还刻有资助者、基层组织者及施工的方法。很可惜,刻在石碑后面的动用夫数、匠工数、捐助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湮没了,字迹漫灭无法辩认。石匠们的工作环境、施工方法,则在后世方志中有零星发现。
宋丰利渠口
如明广惠渠工程施工方法和工作环境,继任的泾阳县令在袁化中(明朝)《开吊儿嘴议》有提到:“抚台项公请自旧渠上於龙山后崖划开,穿山为腹,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顽如铁,工作甚难,日用炭炙醋淬,乃举凿焉,故名铁洞,洞深者百余尺,浅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宽仅四尺,工役仰视,不见天日”。
在《重修广惠渠记》里也有记载:“副都御史项忠请自旧渠上并石山开凿 一里有余,就谷口上流引泾入渠……役者衔篝灯以入,遇石刚顽,辄以火焚水淬,或泉滴沥下,帽戴笠披蓑焉”。
施工之时苦不堪言,工地自然环境也让人不禁悚然。乾隆年修《泾阳县志》记载张家山自然环境,“况自谷口,峭壁悬崖,阴风凛栗,绝少居人。”可以想象那些利夫及石匠的饮食、起居、工作如何的艰难。
石匠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山腹中需人工照明,暗无天日,石质又坚顽如铁,所以该工程标段又被称为“铁洞”。山腹又极为阴森,脚下又有泉流,石渣出入很不不便。山腹之中,有数量不少的凿工、还有运输石渣的民夫、也有在上用绳索拉扯石渣至岸的民工。又因为石洞极狭,最窄处仅四尺,脚下又深浅不一,极不平整,更重要的是还有淙淙泉水,阴冷潮湿,而且还有插在石壁上火把,放出的烟雾弥漫于狭小的空间,再加上通风不利,由此可见这里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
汉白渠口
如此的恶劣的工作环境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人身安全也难以保证,洞中的积水,阴冷湿滑,且脚底深浅不一,深者百尺有余,浅者也要五六十尺,稍不小心就可能滑倒,所以溺水而亡也应该非常普遍。除此而外,工作、居住处于深山,饮食也在山上,暑热风雨都没有办法避开,因病而殁也是经常性的。然而就在关系到数十百万群众生计的水利工程面前,所有个人问题都变得不成为题。虽然对于石匠来说官家有优厚的工资待遇,“一斗石渣一斗钱”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都有不小的诱惑更何况当时。但请不要忘记,在广惠渠断断续续的十七年工程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钱回人不回”。
“钱回人不回”,残酷而无奈,如果没有了性命,钱再多又有什么用。传统的国人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着,年少时“父母在,不远游”;中年时,有家有室,为子女而活着;待得老迈之际,才可以得享天伦,那也得给儿子看护子女。泾阳此地自古不产石匠,因此引泾的众多石匠均来自县域以外,要说关中石匠多的地方首推是富平县,当然还有其他县域。这些石匠抛家舍子,在非人工作环境中拿命换钱,能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工程最后,拿着血汗钱回到家里,没有人知道。但那被称为石匠坟的地方却说明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到被埋在了引泾渠畔,留下的只有孤零零的一座乱葬岗,没有姓名,没有后人四时八节的祭拜,这对于以乡土观念极强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
在今天,当我们缅怀那些为民生疾苦奔走的古代水工和以生疾苦为已任的正直儒生和官员时,不要忘记长眠在山岗上的石匠们,他们也是真正为引泾工程负出的一个群体。他们比那些文人付出的更多,没有了家庭,没有了温情,失去了人生的一切,甚至到现在也没有碑志,没有名字,连后人都不来祭拜。如今,他们的坟茔静静的留在那野花烂漫的山岗,在酷寒暑热中经历风雨,备受煎熬。愿我们后世享受水利雨泽的人们,工作之余徜徉张家山,感受自然气息,摩挲碑刻感受古仁人志士宏大志向之余,也为他们奉以沉思注目,略表敬仰之情,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2016年4月1日晨
修改于2019年11月2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