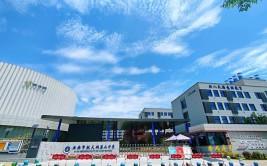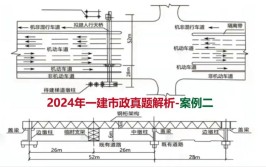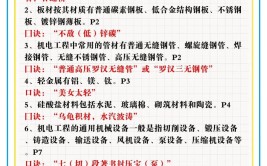忽然想到唱那首《妈妈的吻》时我还是个孩子,转眼这首歌从问世距今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了。
回首这四十年的时间,可真是够久远——当年不到三十岁的的父母亲如今已是年逾花甲,当年刚刚背上书包走进学堂的孩童,也从鬓边生了华发。
而翻检我们的生活,也沧海桑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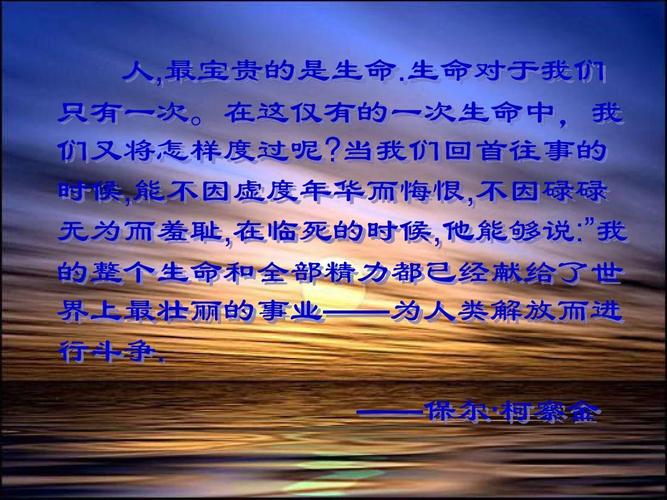
四十年前,“楼下楼下,电灯电话”曾是我们的终极梦想,谁又能想到四十年后,年过七旬的父亲在村里能用智能手机微信和在外地的我们视频聊天?
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是位于黄河岸边高青县唐坊镇一个偏远的村庄,离县城和镇政府分别有大约十公里左右的距离。我家祖辈都是农民,靠种地谋生。
四十年前我们的村子里没有电,交通也不方便,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县城是我们见过的最繁华的城市,但一年中也去不了几次。和远在外地的亲戚之间的联系,只有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通信和春节前互寄的土特产。
1978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孩子多,日子过的很是拮据,五毛钱的书费学费拿不出,要跑好几家去借。
那时候的夜晚很黑。我们在学校里上晚自习时,一人提一盏煤油灯放在桌上,是那种墨水瓶加个酒瓶盖钻个孔穿上条棉线做的灯芯的煤油灯,每天晚上,我们的鼻孔里都是被煤烟熏的黑黑的,回家想多看会书,大人们也会心疼,嫌“点灯熬油”的,只能早早吹了灯睡觉。我们的课本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那种生活让我们羡慕,觉得那就是天堂了。
八十年代初我们家终于买上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和外面世界建立的联系,对更大更远的世界的了解,就是通那一台小小的收音机。
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后,我们家有了自留地,开始是种粮种棉。后来又拿出一部分地用来种瓜种菜。高青水土好,种出来的西瓜特别甜,很受欢迎,也让我们家尝到了甜头原来贫穷的日子开始慢慢好转,八十年代末,成了村里最早富起来的几个万元户之一。
1986年夏天,村子里通上了电,从此乡村的夜晚亮了起来。1987年春节,我家看上从县城买回的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成了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家有电视机的人家。那年除夕夜,我家的屋子里挤满了来看春节晚会的乡亲,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就在那一年火了。
刚开始电视上用室内天线信号不好,满屏的雪花点点,声音咝咝啦啦,于是又买回了室外天线,绑在窗外树起的一根大木杆子上,比房顶还要高出去一块。看着看着,如果画面不清楚了,就有一个人跑出去抱着杆子来回转,调整天线的方向,遇到大风天气,刚调好就又吹偏了,特别烦人。
到了那年夏天我们家又买了一台蝙蝠电风扇(风扇质量不是一般的好,一直用了二三十年)。
就这样慢慢地,黑白电视被淘汰,换成了彩电,再有了VCD、DVD,喜欢唱戏的父亲装备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更新换代,MP3、播放器都有了。
大约是1998年装上了程控电话。大年三十晚上往家打电话拜年,一家人都很兴奋。
慢慢地,手机电脑都不再是新鲜物件,父亲用上手机也有十几年了吧。一代代的手机不停地更新换代,父亲的手机也从移动电话变成了可以用微信看视频聊天。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进城工作,在城里买房安家。但是像父亲这个年龄的村里的老人们都不愿跟着孩子们去住楼房。他们觉得高青农村的平房大院才是最养人的地方。
在院子里种些青菜养些鸡鸭,没事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吹吹凉风,和远方的孩子们用微信视频聊聊天,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
从逃离土地的急切,到渴望回归的慢生活。
作为在高青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一代人,我们对于土地的感情,真是又爱又恨的。土地给了我们粮食,给了我们收获的喜悦,但是,也给了我们自卑的身份,让我们尝够了日复一日烈日和风雨中的劳作之苦。春耕秋种,灌溉施肥,锄草割麦,喷药捉虫。我们的日月光阴里,不是负重低头前行,就向大地躬身弯腰。
我记得犁铧怎样翻开黄土地。
我记得黄河水怎么样通过抽水机从沟渠流进田垄间。
我记得小麦玉米和棉花以及瓜果蔬菜的种子怎样破土钻出地面长出幼苗。
我更记得烈日下镰刀划过麦杆汗水湿透衣背的煎熬。
记得寒风中伸手摘取棉花上最后的棉桃被扎裂手指的疼痛。
我记得丰收的粮食如何在汗水中颗粒归仓。
记得麦收后乡亲父老拉着一车车的小麦去粮所交公粮时生怕交不上的焦虑。
记得排着长长的队去卖棉花等待检验时的忐忑。
记得农闲时青壮劳力出夫疏浚河道时一身泥一身水的辛苦。
……
那时候,家乡有多少女孩子想嫁到隔着一条小清河的桓台,因为那个号称吨粮县的人农业机械比我们先进,可以不用受原始的劳作之苦。
那时候,厂里的工人,商店的售货员都是我们羡慕的人群,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身上不沾泥水,能穿干净衣服的生活,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改革开放前,作为农家的子弟,都像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样,被农民的身份所累,为了考上个中专和大学有个非农户口头悬梁锥刺骨地苦读,一旦跳出农门就抛弃了在老家种地的未婚妻。你不能说他们现实,因为大家都,苦怕了累怕了,穷怕了,不希望子孙后代也过那样的生活。
九十年代初城镇户口一放开,多少农村家庭毫不犹豫地拿出半生的积蓄,去给孩子买一个城镇户口,以得到一个安排进县城里工厂工作的机会,以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人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城里的人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政策放开,农民的孩子们也纷纷走出土地进城闯天下。潮涨潮落,成功失败,每个人的生活都开启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变化。
农村和农业也在悄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种植养殖,土地流转,那片土地上出产的作物也都有了自己的品牌,西红杮西瓜桃子大米等农产品都名声在外了。耕种和收割,都逐渐实现了机械化,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乡镇和村庄都有了加工企业,留守土地的人们也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而我们这些当年拼命逃离土地和乡村的一代人,在城里生活了若干年之后,也开始渴望回归故土享受在院子里种菜养鸡晒太阳的慢生活了。
想回“慢城”,回到从前的慢。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慢”也是一种奢侈。
常常怀念从前的慢。
在那自行车都稀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里,我们走亲戚,赶集上店都是步行,去十公里外的县城看病、赶集买东西,都是步行去。如果需要运货物,则或推着独轮车,赶着老牛车。
我上初中的地方在唐坊镇,当时叫唐坊公社。开学父亲赶着车把我的床板和被褥拉到学校之后,每周回家我就靠自己的双腿了。周日的下午,背着娘蒸好的干粮和一罐咸菜从家出发走到学校。每周六的下午再从学校步行回到家里去拿下周的干粮。通往学校的那条路开始的时候还是土路,遇到下雨天就泥泞难行。等我们毕业时,它就铺上了沥青,也通了一辆开往县城的公交车。现在呢,现在那条路比当初已经拓宽了好几倍,还与滨博高速公路的出口相连。
县境内所有的路,正在越变越宽,越变越平坦,四通八达,与外面广阔的世界连接。
当年我们最盼望的日子是每年秋天赶物资交流大会,早早起床,成群结伙往县城走。在那些卖布的卖百货的摊前转啊看啊比啊,不买也觉得很满足。走累了就花几毛钱买张戏票进去剧院看场戏。看完戏出来在包子棚里买几个包子吃,就是一年中难得的精神大餐和物质大餐。然后暮色中,再慢慢步行一两个小时回到我们的村庄里去。有了自行车后,遇到节日里没处玩,跑到县城去看场电影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的享受了。
那时的县城也不大,就几条街就走遍了。
县城最难忘的味道是酒厂的酒糟味。我们从东南方向未进城先闻着那个味道。县城里最熟悉的一条路是是文化路,路东面是百货大楼,路西面是新华书店,往南是一中、邮电局、剧院,招待所、文化馆……
1987年冬天我曾报名参加县文化馆的声乐培训班,晚上住在剧院后面的二层小楼上。早上去招待所吃饭,午餐喜欢去那个大棚搭建的商城里吃两毛五一个的樊家肉烧饼。肉馅很肥,烤得黄黄的很香很香——这么多年,再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烧饼呢。那一年冬天,我还去过几次一中的教室里看望那些在里面上学的同学,他们埋头苦读的样子真让人羡慕。
1988年元旦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文化馆东门外的那条沙子路上铺满了雪,那些树枝也都成了白的,我们几个学员在雪中嬉戏,在沙子路树下拍了几张照片。我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那些照片,这三十年来,我一直觉得那张照片里应该有我青春岁月里留下的最美好的笑容。
后来的日子里,我跟着父亲去县城卖瓜卖菜,买煤买肥料。我们赶着驴车,来来回回,怎么也得大半天的时间。那时候觉得住在这个县城里真好啊,生活真方便。
现在,那个当初只有几条街的小县城,不知扩大了多少倍,长高了多少倍,想转遍小城,得坐公交车了。村里现在几乎家家都有了机动车,上个县城很方便了。
县城的风貌以前古朴寡淡,如今,高楼林立,颇有些现代和繁华的意思了。再有环城水系,园林绿化也做的好,花草绿荫掩映着楼群,一泊千乘湖畔风光无限,与早年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县城那些可亲可爱的人,县城在我心里也是可亲可爱的,是将来退休后可以归去的宜居之地。“慢城”的名头近几年叫的响了,我这在外的游子,十分迫切地想回到它的“慢”里去。
不止一次地想,退休以后,回县城去住。在“慢城”中漫步,慢慢地,回忆从前,慢慢地,享受现在。
这样的生活,想想觉得很惬意。
(本文配图均来自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