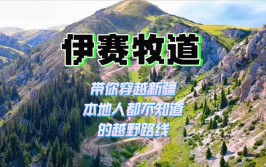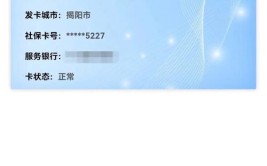那首歌很美,听着想流泪,不仅是为了王琪唱出的哀怨情伤,也是为了那拉提。我在新疆当兵时就在那里。虽然已过去几十年,现在闭眼回想,似乎还能看到那里的山景水色,茫茫草原,还有雪山脚下我们一手建造的大营盘。
那年我十七岁。中苏边界打起来,一次在黑龙江珍宝岛,另一次在新疆铁列克提。我报名参军,晚色中登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军列。列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向西北开去。我们不知终点是哪里,只知道要去打仗。
列车跑了七天七夜,停在了乌鲁木齐一个车站。带兵人说,我们到了,大家下车。火车跑了一日又一日,潜意识中感觉这车永远到不了终点,突然到了,竟有些不适应。下了车,外面出奇地冷,感觉寒气穿透了棉军装。第二天换乘军用卡车又跑了两日,终于到达目的地伊宁市。

伊宁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自治州紧靠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面有苏军七个机械化师。驻守伊犁的是陆军第七师。兵力大都部署在新源县和尼勒克县,距伊宁市200多公里。20团驻地在新源县的那拉提山下,但把我们二营单独派到伊宁市。那里离边界不到一百公里,是最前沿。
当年陆军第七师驻军伊犁应对入侵
从东部沿海一下子来到伊宁这个西域边城,一切都那么新鲜。这里不像乌市那么冷,地面积雪也不厚。微风带着凉意,却不刺骨,感觉像是东部沿海的冬季。街景却与沿海大不同。房屋全是异域风格,有点像电影上看到的俄罗斯城市。玻璃窗外加一层木板窗,漆着鲜艳的颜色。想是夜间要把木板窗关闭。街上跑着欧洲古典样式的四轮马车。木制车轮包着铁箍,跑起来震天动地响。车夫威风凛凛,一脸肃穆。许多驴车在街上悠然徜徉,赶车人也不似马车夫那般昂然,给这座小城染上几分悠闲。
街面上男人一律黑色棉衣和长筒皮靴。女人除了棉衣和长筒靴,还有五颜六色的长裙。记忆中各地男人都是差不多的灰头土脸,女人是区分一地的标志。伊宁更是如此,女子们用多彩长裙和发髻告诉我们,这里是西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伊宁市斯大林街
二营驻扎在自治州党校。除了驻防,还负责伊宁市重要单位的军管。政治运动中各派互不相让,甚至动了步枪、机枪和炸药包,只能靠军管稳定局势。两年后二营完成任务调回那拉提,于是我有幸见识那一爿眼下被千万人传唱的美丽草原。
伊宁到那拉提200多公里,二营全靠两条腿走去。师部派来的几辆卡车只够运货。我们经过多次行军训练,这点路不算什么。有次练习强行军奔袭,一夜走了70公里,到终点后全都累得爬不起来。
正值夏末秋初,天气十分清爽。部队不紧不慢地走在公路上,沿途欣赏着伊犁河谷的大好风光。说起新疆,都知道雪山、沙漠和茫茫戈壁滩。伊犁却十分不同。翻出地形图看看,群山之间有一大片喇叭形谷地,那就是伊犁河谷。雪山融水汇入伊犁河,滔滔向西而去,千万年冲刷造就了伊犁河谷。高山挡住了自北而下的寒风,自西而来的暖湿气流又为河谷送来充沛降水,使之成为西域江南。这里盛产粮食、瓜果、牛羊,还有驰名中外的伊犁马。我们沿着公路行军,隔不远就一个村庄。路边排列着高大白杨树,时时有少数民族老乡赶着马车驴车经过。完全不似新疆别处那样空旷荒凉,倒像是沿海乡村景象。
公路边排列着高大的白杨树
伊犁河谷东端是喇叭形谷地的尖端处,也是伊犁河的发源处。那里的山脉叫做那拉提山。20团营房就在山脚下。我们越往东走人口越是稀少,天气也越是清凉,接近那拉提时竟有丝丝寒意。那拉提山海拔3000米以上,远远望去,能看到山上的雪线。山下有条蜿蜒河流,河水清澈见底,岸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白桦林。那是伊犁河直流巩乃斯河。向北看去是大片草原。无数牛羊点缀于草地,怡然低头啃食,一支大军开过来,全然视而不见。
那拉提位于伊犁河谷东端
巩乃斯河蜿蜒而去,汇入伊犁河
金秋那拉提
秋季那拉提虽无春夏季遍地鲜花,却另有一种美色。哈萨克牧民趁苜蓿草枯黄之前挥舞着大镰刀打草,为牛羊准备过冬饲料。待寒风渐渐袭来,大地变成一片金黄,在雪山和松林衬托下显得格外圣洁。
如果我们是游客,可以选最好的季节前来,在此逗留数日,餐餐佳淆,在在美景,然后潇洒离去。但我们是军人,要在此驻防,还要自己建营房。于是,我们还能见识那拉提的另一面。
那拉提的冬天来得很早。这里平均海拔1800米,地面比泰山玉皇顶还高。十月是沿海的金秋时节,这里已下了第一场雪。到十一月,大地已是白茫茫一片,与远处的雪山浑然一体。只有松林依然苍翠,镶嵌在群山之间。
那拉提的初冬
隆冬时节的那拉提
部队又该上山伐木了。建营房需要很多木料。林业部门给了伐木指标,要求间伐,就是隔多少米砍一棵树,以保障自生树苗有树荫遮蔽不被晒死。那时没有机械,全靠大斧子生砍。也没有运输车,要几个人一组,拉着绳子跑十公里把一棵棵去掉枝叶的大树拖回营房。于是只能在冬季伐木,大树可在积雪上像雪橇一样滑行。
二十团需要自己种菜吃。师部在则克台有大型农场,有时会送些白菜过来。但运输能力不足,巩乃斯河水上涨时,还会把自己建的木桥冲垮,二十团主要还得靠自己。
那拉提的气候对植物很挑剔。黄瓜长不大就变黄。我才知,明明是绿色的一根根为什么叫黄瓜。白菜总长不大,西红柿长到老死也不红。据说总吃青涩西红柿会中毒。那拉提却偏爱植物的地下部分。土豆能长到一两斤重。卷心菜的块根长得像萝卜,各连都把它腌成咸菜。四川兵说,吃起来像四川榨菜。最出奇的是大蒜,大如拳头。生猛如山东兵,一瓣生蒜也吃不下。有一年冬天,不知为何别的菜都没有,吃了一冬腌大蒜。至今想起来还反胃。
乘火车西行,出了玉门关,眼前一片茫茫戈壁。王之涣的 “春风不度玉门关”便是生动写照。新疆大部分地区同样是一片干旱少雨景象,伊犁河谷却非如此。在伊宁市就发现,夏季虽不像东部沿海那样大雨倾盆,也断不了下场像样的雨。有次我们练习野外露营,半夜下起雨来,雨水灌入帐篷,连长不得不下令收兵回营。
那拉提的小气候更是令人瞠目,雨水比伊宁还多。本是晴空万里,不经意间发现远处雪山上升起白云,然后白云逐渐扩散变成乌云,不多久便是乌云满天下起雨来。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爽。过几天又来一次同样情景。我甚至怀疑那拉提的水蒸气哪里也不去,就在本地循环往复,好像处于一个巨大玻璃罩之中。
乌云自雪山顶升腾而起
那拉提常见的局部降雨
那拉提雨水多,昼夜温差大,土豆、大蒜、卷心菜长得好,我想这正是原因所在。当地哈萨克人并不种这些。以前哈萨克牧民都是拉着蒙古包逐水草而生,后来大都定居在村中,住着干打垒房子。可是他们没有农耕习惯。身边就是巩乃斯河水,也不知道引水灌溉。部队派了一个连,只用三天就为村子挖好一条数百米水渠。村民好吃惊:原来农业可以这样做。
哈萨克人的主食是小麦做成的囊,就着奶茶吃,就是那种用鲜奶和四川茯苓茶煮成的奶茶。吃饭时在屋内地上铺一块餐布,一家人就地围坐一圈。他们很少吃蔬菜水果,没有这个习惯。部队卫生员说,不少人得了坏血症。
他们也养鸡养鹅,但不吃鸡蛋和禽肉,都是拿去卖,卖得非常便宜。他们养的是那种能飞上天的鹅,看上去有点像鸿雁,肥肥大大的,助跑好几十米才能飞起来。
有些哈萨克人在山里养蜂。《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中有个让男主无法释怀的养蜂女,感动了无数人。那拉提人的确有养蜂习惯。春夏之际,漫山遍野的鲜花提供了无尽蜜源。我买过一瓶蜂蜜。准确说不是买的,是拿部队自产烧酒换的,一瓶酒换一瓶蜜。养蜂人是个哈萨克汉子,嗜酒如命。那时哈萨克姑娘似乎不养蜂。歌中唱的养蜂女弃他而去,那是多年以后的故事。
而今的那拉提养蜂女
我喜欢那拉提的大山。在营房内透过窗子就能遥望远处的崇山峻岭。那终年积雪的山峰不知藏着多少秘密。有空时我和战友会带上冲锋枪进山。据说山里有野兽,有狼或是野猪,带上枪才敢翻越一个个山头深入密林之中。可是除了各种鸟类,我们从未遇到过其他动物。也许那些动物听到人声早已远遁。
有时我也会独自进山,不带武器,就在山口不远处静静地读书,伴着鸟叫和树叶的飒飒声。有次读得忘情,抬头发现西边落日已快隐没。这时才突然想到,天黑后一个人待在山里是什么感觉。好在离山脚不远,顺山间坡路匆匆而去。
同样难忘的是那条蜿蜒流淌的巩乃斯河。浅浅的河水,冰凉沁骨。雪山融水流到这里,还未来得及从阳光中吸取足够的温暖。河床中全是大大小小的卵石。军车空载时可以压着卵石涉水渡河。沿河而生的白桦林倒映在清水中,让河流多了几分秀丽。不远处还有大片苹果园。记的有一年五一节后还下了场雪,我们特意赶到苹果园拍照留念。一朵朵白色苹果花与枝头残雪浑然一体,说不尽的妩媚。
朝霞中的巩乃斯河
巩乃斯河还为二十团提供了廉价电力。以往是用柴油机发电,那电宝贵得很。每当熄灯号响过,全团电灯一下子全灭。不睡觉的只能点蜡烛。我常在熄灯之后靠蜡烛读书。
后来买来水力发电机,在巩乃斯河落差较大处建了个小水电站。电力源源不断,二十团用不了,就把电线拉到那拉提镇(那时叫那拉提公社)让他们分享。哈萨克村民高兴坏了。那里远离城市和工业区,谁也没想过竟能用上电。通电那天团部特意搞了个仪式。哈萨克人老老少少骑马赶来,还带来自制的马奶子。哈萨克少女翩翩起舞,就像盛大节日。
那年新疆军区文工团来二十团慰问演出。漂亮的女演员们混在灰头土脸的士兵中,公主般地闪着光。听惯了靶场的枪声和营房工地的噪杂声,演员们的歌喉似天籁之音,把大兵们带入从未体验过的境界。每连只有连部一台收音机,只在晚间集会时放放,多年来音乐与大兵无缘。著名歌手李双江唱了一曲《八路军拉大栓》,从此让我记住了他独特的颤音。
士兵们掌声雷动,让演员们也很兴奋。他们没想到,深山中竟隐藏着一个叫那拉提的仙境之地,还有两千多土包子大兵忘情地欢迎他们。第二天,李双江躺在冰冷的巩乃斯河水中,冲着白云引亢高歌,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其对那拉提的莫名之情。
那拉提的群山是战时最好的屏障。二十团是全师的总预备队。一旦入侵者大举进攻,前线部队顶不住,他们可以撤到那拉提,然后撤进山里。这时就该由我们二十团杀出来阻击,掩护主力部队撤离。
战时的屏障平时却成了交通障碍。自那拉提向东北方有一条山间公路,一直通向独山子和乌鲁木齐。那正是现今独库公路北段的前身,六十年代建成。山路崎岖险峻,途中还要翻越雪山,只在夏季可以通行,其他时节不得不向西逆行,取道伊宁市,然后绕过果子沟和赛里木湖再折向东方。那正是我们入伍时走的路。于是,几百公里路程变成了一千多公里,原本可当天赶到乌市,这下变成了三天。
由于大山阻隔,不得不绕道上千公里,经伊宁和赛里木湖去乌市
有年夏季,团政治处派我去乌鲁木齐出差,恰好有辆军用吉普载一位军官也去乌市,要翻越雪山直达独山子。早听说山中藏着一条神秘公路,时常遥望着群山,想象那条路究竟什么样。这下好了,终于得以一见。
山中的路总是曲曲弯弯,依地势而行,这条路同样如此。路很窄,勉强能会车。好在我们根本无需会车,那辆吉普如同独行侠,在苍翠幽静的群山中踽踽然游荡。
独库公路 1
独库公路 2
没走多远便看到瀑布,然后又是瀑布。多年后见到的伊瓜苏大瀑布有种震天轰鸣的气势,此时的小瀑布恰恰相反,涓涓细流给人以幽静恬美之感。无数小瀑布汇成公路下方的溪流,想来应是流入巩乃斯河,最后汇入滔滔伊犁河进入哈萨克斯坦。
吉普车越爬越高,不觉间已进入雪线之上。天上开始飘起雪花。司机打开暖气,车内外是两个天下。同车军官指着窗外说:那里有雪莲。果然,一朵雪莲花在路边高处开放。早听说天山雪莲,没想到雪莲花竟能孑然一身于雪地。心想:它不感觉孤独吗?
孑然一身的天山雪莲花
翻过雪山后,车速明显加快。下山后便是通向独山子和乌鲁木齐的柏油公路。这是我在新疆城区之外见到的唯一一条柏油路。路上跑着连绵不绝的油罐车。独山子有克拉玛依的炼油中心。那时既无铁路,更无管道,全靠油罐卡车日夜奔跑,把原油从油田送往炼油厂。从那拉提来到工业区,有种自天外回到人间的感觉。
这条那拉提到独山子的简易公路如今已翻修成独库公路北段。独库公路开工时,恰逢我们这批兵摘掉领章帽徽,准备退伍回家。我们连被调去参加公路施工。不久听说有个新兵在塌方中遇难。那个兵我熟悉,很帅气的小兵,见人就笑。我心里好难过。
登上送退伍兵的军用卡车,还有点依依不舍,心里在默念:别了伊犁,别了那拉提,不知何时才能重返这一爿仙境。
(文中插图取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