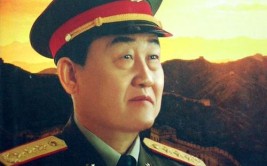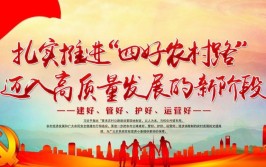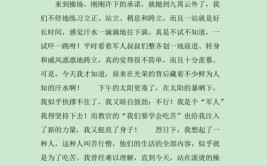——青藏线上的故事(六)
作者:杜锦超
青藏线是什么?

是戈壁、雪山、草原……
是牦牛、雄鹰、藏羚羊……
是公路、道班、兵站……
是青春、热血、奉献……
是西藏的命脉,是祖国的尊严。
雪花飘洒着军人的梦想,黄沙掩埋着岁月的辉煌,三江源河水流淌着一串串平凡的故事,扎木聂(藏旋弹弦乐器)声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高原上的老黄牛
代可国,原汽车一团供应股股长,重庆市铜梁县人,1946年8月出生,1968年3月入伍。他中等身材,国字脸,为人忠厚善良,诚实热情,言语不多,外号人称老黄牛。新兵入伍他被分到三营10连炊事班。在炊事班他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自己动手腌制咸菜,磨豆腐,调济伙食。还利用空余时间一锄一锄地开荒帮助连队扩大菜地面积。
1972年5月,他由10连司务长调任团后勤处供应股任助理员。当年秋天,团里让他带领修理连和司机训练队各一个排的战士,到江西沟生产队搞秋收。经过30余天夜以継日的奋斗,3800多亩庄稼收割完毕。当年风调雨顺,收成特别好,共计收获油菜籽42万多斤,靑稞、豌豆16万多斤。粮食丰收了,代可国体重却减轻了8斤。
代可国(右一)和战友在一起
“军队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已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交换的产品⋯"根据毛泽东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汽车一团农副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先后在西大滩、可可西里、沱沱河养牦牛200多头,养羊1200多只,增加了团队3000多人的副食供应,解决了长期见不到"油水",解决了让战士们吃饱吃好的问题,减少了"空头政治"对部队建设的冲击。
每年11月10日,是汽车一团与索柴一家(聘用放牧的藏民)法定上山杀羊的日子。从1974年至1979年连续6年代可国带着4名战士执行这一光荣任务。杀羊,不知详情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个中苦衷有谁知晓?通常这些牧场都在海拔4200米以上,离青藏公路近的有几十公里,远的则100多200公里。到了那里,只能跟着藏民一起喝酥油茶,吃粘粑和半生不熟的牛羊肉;晚上睡在零下二十多度既透风又漏雪的"解放大楼"(汽车大箱)上。杀羊,首先是在索柴的指认下,用红墨水给该杀的羊作记号,然后,一人抓住羊头,一人抓住羊的后腿,两人同时用力将羊放倒并压住,再一人挥刀杀羊。羊血流尽后,用绳子将羊头套起来拖到木桩边,再挂起来剝皮,开膛取出內脏。羊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看到同伴被杀死,整个羊群会发出同情的"咩咩"叫声,当你去抓第二只羊时他会拼命反抗。一只羊100多斤,力气很大,由于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作业,一用劲立马就会头昏眼花,杀死一只羊,人也差不多昏死一次。青藏高原的冬天,风大、雪大、缺氧、零下20~30度的严寒,杀300多只羊,30多头牛,最快要7天,一般情况都得10天才能完成任务,10天下来,身体再好的都得瘦一大圏。
1977年,西藏那曲地区工商局与汽车一团簽定三年协议,每年供给部队二万斤牛羊肉,单价每斤0.27元,条件是部队每年11月杀羊的季节开车去海拔4500米的索县和巴青县收购。1978年,代可国刚刚完成自己牧場的宰杀任务,休息了两天,又第二次带車去黑河巴青县收购牛羊肉。车到黑河兵站,再往东200多公里收购牛羊肉返回途中,离青藏公路还有10多公里的地方,由于便道坑坑洼洼,汽车水箱下水室出现裂缝,水漏光了。焊接好水箱后藏北草原一片白茫茫,无法寻找水源,代股长只好让驾驶员留下看守车辆和车上的物资,他和后勤处战士杨树亮走出草滩背上水桶前往道班要水。
代可国和家人在一起
晚上8点多钟出发直到12点才找到道班。可是敲了半天的门却沒有人答应,不知道是风声太大还是睡得太香,代可国他又冷又饿,只好找根棍子一边敲门一边敲水桶,足足敲了半个小时,道班工人才开了门。代股长说明情况并再三央求,道班才很不情愿地将自己羊皮口袋里不多的饮用水给了大半桶。此时已是零晨一点,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刻。
天上飞舞着大雪,代可国他们轮流背着水桶高兴地往回走,走了不到三公里,风越刮越大,雪花越飘越紧,前进的阻力一步一步地增加,累、冷、餓、缺氧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代股长他们的腿像罐了铅一样沉重,实在迈不开歩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这时他明白千万别躺下,不然会冻死,他让小杨将水桶(汽车兵专用的扁桶)上的绳子解开捆在自己腰上,一步一步水桶往前爬行,风稍为小一点,他们赶紧起来拖着水桶往前走。就这样坚持走到零晨四点多终于将水拖了回来。而留守的战士在驾驶室里耳朵冻肿了,腿冻彊了,下不了车,代股长赶紧将那两条像冰棒一样的腿插进自己怀里,用皮大衣包裹起来,并帮他揉槎捶打,好不容易才有了知觉,最后终于把牛羊肉运回团里。
人们那里知道,就在代股长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二天,他的夫人肖先碧带着三个孩子来部队探亲了,一等七八天不见人回来,心里着急,再加上旅途劳顿,患上了急性甲型肝炎,被送往22医院治疗。
当代股长拖着一身疲惫,走进自己寝室,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床上被子没叠,桌子上碗筷没收,三个孩子拥在一起哭成泪人。猛然间走进一位又黑又瘦的人来,三个孩子一下懵了,片刻大儿子洪成回过神来,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三个孩子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刷地扑了上去,哭声又响了。"你妈妈呢?"。 "住院了",儿子细声的回答像一声惊雷,代股长瘫倒在地上,两只眼睛像山涧的清泉,默默地往下流淌。
三个孩子的齐声呼喊,三个孩子的齐声痛哭,引来了叔叔、引来了伯伯,引来了卫生队的救护车。积劳成疾,过度疲劳和透支,"老黄牛"累倒了,被送进了22医院。当护士给他静脉注射时,药水怎么都推不进去,医生护士流着泪,说:再晚一点可能没救了,血管里的血液缺水流不动了。
站上世界屋脊的军嫂——刘淑碧
话说军嫂,得先从兵哥哥说起。
原汽车一团三营九连指导员王邦才,重庆市铜梁县人,1949年出生,1968年3月入伍。他中等身材,四方脸膛,皮肤黝黑,脸上时不时冒出几颗青春痘,操一口"红烧"普通话。
王邦才在车场讲解车辆养护
9连自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换装解放牌汽车以来,继承连队爱车光荣传统,在历届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车辆,出车率平均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年年超额完成运输任务,新车第一次大修平均间修里程22万公里,大修平均间修里程7万公里。至1977年,共计节约材料费、维修费87万余元。培养和造就了"雷锋式战士"汪龙兴等一批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的优秀战士,养护了安全行车60万公里无大修的30号车,成为全军先进典型。连队多次被评为"爱车标兵连"、"车管先进连"。作为先进代表,两次出席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先进经验。1977年、1979年两次被总后勤部评为"硬骨头六连式连队",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四次被评为"四好连队",两次被评为"双学先进连队",《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以"雪山雄鹰"为题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他和连长万学生一起曾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四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78年双双被评为"模范连长"、"模范指导员"。
王邦才与爱人孩子合影
1980年11月,王邦才从西安开会回来,准备回家探亲,这时一纸调令调他去拉萨大站当雄兵站任教导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工作交接完毕就去了海拔4200米的新岗位,改行做起了为汽车兵服务的工作,兵站工作任务繁重,干部和战士都缺编,在不经意间三年没回家了。其妻刘淑碧心里犯嘀咕,是生病了或是受伤了?再忙也不能把一家老小忘了。于是他将家里老人和孩子安排妥当便出发了。从农村老家坐汽车到县城铜梁,从铜梁再坐汽车到永川,转乘火车到陕西宝鸡,再转乘火车到青海西宁,到西宁转运站等待搭乘去格尔木的汽车,到格尔木大站再等待搭乘去拉萨的汽车,一路颠簸,已经14天了还没见到亲人。那天汽车从唐古山兵站出来不久,天上大雪越飞越密,驾驶员凭他多年的経验,预判有可能大雪封山,劝她返回兵站避一避,等待天气好点再走。心急如焚的军嫂刘淑碧,那里听得进这种话哟,她不听劝阻执拗地坚持下車,背上行囊沿着公路歩行前往。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风紧、雪寒、雹急、缺氧,军嫂刘淑碧凭着一腔热血和韧劲,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精疲力尽的军嫂摔倒了,但她又坚强地从雪地上爬起来,继续前进……当她最后一次爬起来时,眼前一遍膝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她竟不知道自己患上了雪盲。但心里还是暗下决心,非要走到当雄不可,她歇了歇,挺直腰杆,摸索着继续前进……当丈夫赶来接应她时,老远就看见雪山上有一个红点,那是她头上的红色围巾在雪风中飘扬……。
30年后,兵哥哥王邦才为妻子写下情真意切的一段动人诗话:
人间情,直教人生死相许?年年万水千山隔,夜夜两心遥语。踏远途,为一晤,雪崩路断焉能阻。凡间民女,对险障重重,鹊桥难觅,承载几多苦。
相思泪,浸泡心田衣被,今朝尤让人妒。柔情融得千秋雪,绝境化天路。风且住,山折服,静观悲壮夫妻聚。边防何固?有大爱支撑,长城似铁,家国用心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