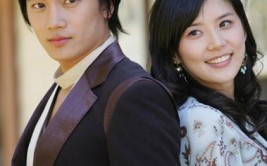“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2020年刚过几天,北京门头沟山高月冷,残雪凝辉。
元月9日,“中国铁建地产集团主题教育汇报展演”在山脚下的忠良书院举行。
这两句是华东公司一群小伙子演唱的《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歌词。
我在现场录了一段视频发给了父亲汪心连,片刻发来语音“听到这首歌很激动,想起了我当兵的时候”。
这首中国铁建的企业之歌,和父亲有什么关联呢?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撤销建制,整体转业划到铁道部,后来成为央企中国铁建。
企业之歌就是原来的铁道兵军歌。
2019年我毕业13年后,履职中国铁建,也算漂泊多年的“铁二代”回家了……
A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一天夜里12点,全师新兵近千人紧急集合。
凌晨三四点,大家精疲力尽的时候,天蒙蒙亮了,营地又出现在眼前,原来他们来回跑了一个圈。
1976年元月,父亲戴着大红花、从敲锣打鼓的人群中走出,在安徽省砀山县坐上新兵专列,经陇海线、过徐州、进入东北大连金县,从此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
“当时不知道铁道兵是干什么的,以为像空军开飞机、海军开军舰一样,铁道兵嘛,应该是扛着枪威武地保护火车、保护铁路。
”父亲回想起以前的事情,感慨万千。
“那一年砀山的兵比较多,大概800多人。
”
到驻地后,履行完程序,父亲分到新兵训练基地。
新兵训练基地的营房距离海滨仅500米,第一次见到碧蓝的大海,海面上海鸥或凌空翱翔,或盘旋着猛地钻入水面。
部队生活一切都感到新鲜,第一次刷牙、第一次叠被子、第一次穿军装,甚至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有规定。
从农村来的父亲散漫惯了,把部队当成熔炉,当成重塑自己的机会。
3月份开始新兵训练,踢正步、站军姿、喊号子。
白天练习有时跟不上,他有时为了一个动作,就利用晚上的时间,一个人去海边自己补课训练。
海边皎洁的月光下,呼吸着潮湿的、咸咸的、冷冷的空气,踩在海边伴有砂砾的道路上,踢出的不仅仅是正步,而是一个年轻人重塑自己的步伐,磨炼意志的步伐。
部队的日子待一段时间,新鲜感就很快散去,剩下的就是重复、单调、枯燥,对于年轻的新兵来说,军营里太复杂的东西往往靠不住,简单道理反而容易留存。
每天早上唱《走向打靶场》,每天晚上唱《打靶归来》,重复也是一种磨砺。
5月份冰雪才开始融化,6月份的金县春寒料峭。
按照计划,6月下旬就进行军训的最后一项野外拉练。
一天夜里12点开始,全师新兵近千人紧急集合。
各团营连依次开始,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背上(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战争电影一样镜头,山海傍依,风高月黑。
他们遇到探照灯就躲开,遇到照明弹就卧倒。
这种体验每个男孩子都想过一把瘾,而真正的滋味却是艰辛的,经过一夜跋涉,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不知道在哪里。
就在凌晨三四点,大家快精疲力尽的时候,夜空中划过一道道流星,东方刚刚露出一线亮色,一会儿天蒙蒙亮了,峰回路转,营地又出现在眼前,原来他们来回跑了一个圈。
百炼成钢,化为绕指柔。
“打铁首要自身硬”,经过新兵营的锻造,他们奔赴“前线”,与钢轨铁道开始了近距离的较量。
B
以铁纪打造铁军
父亲连队与地方军民共建,结“鱼水情深”。
帮助当地村庄盖了一所学校,村庄回馈子弟兵,专门划出一块草原,让部队收草喂养军营里的猪、羊、驴等。
新兵训练结束后,父亲开始“下连队”。
乘坐部队专列,从渤海边的大连去了科尔沁沙漠草原边的通辽,从通辽坐汽车到东来的营部,营部又分配到位于余粮堡的连部。
正式进入“第二条东北入关铁路——北京到通辽线,负责东来站到西六方站之间约40公里长的“施工战线”。
余粮堡不是“剩余粮仓的意思”,只是一个普通的公社,曾是上世纪“闯关东”落脚点之一。
先民在地上掏个洞,上面用树枝树叶等东西遮挡,半地上半地下的窝当地叫“堡”。
部队不住“堡”,也不住“房”。
一座座帐篷,搭起了四四方方的军营。
9月,科尔沁沙地草原东部就早早变冷,夜晚的冷风嗖嗖冻人,西伯利亚酝酿生成的冷空气到东北算是刚刚“出城”,劲头正猛,刮起风来如东北虎在嘶吼,裹挟着鸡蛋大小的雪片拍打着帐篷顶部,帐篷常常被吹得左摇右晃。
雪花落地后也不再融化,一场接着一场,一层覆盖一层,直到第二年5月份才开始冰雪融化。
在东北大兴安岭的“生命禁区”,铁道兵发明了“地火龙”取暖。
在科尔沁草原也是靠“地火龙”度过漫长冬天。
父亲解释说:“帐篷四周围了一圈走火的通道,类似于放倒的烟囱,草原上最低温度在-20℃,帐篷内温暖如春。
”
一个帐篷里有一个大炕,一般睡8-12个人,平均每个人睡觉的地方不足1米长,战友们个个躺得笔直,像超市码齐的黄瓜一样一个贴着一个,军队塑造人从内心到体型是很全面的。
时间一长,大家都熟了,晚上神侃各人家庭经历,推心置腹无所保留,成为后来的知心好友。
东北人秋天就开始储备过冬的物资,普通人家吃的是土豆、大白菜。
部队也面临物资匮乏,每人每天伙食费1到3毛钱,入冬就常年吃美其名曰的军备菜,就是干菜、萝卜缨子、咸菜等。
为牛羊准备的过冬物资就是草料了。
入秋以后的科尔沁沙地草原,干草遍地,有的地方比人还高。
当地牧民用一种特制的钐刀,然后安上白蜡杆,扭动腰部、腿部和胳膊,一起配合,旋转半圈180度,眼前的干草齐刷刷地倒下。
除了修铁路以外,每个班都分配了收草任务。
有一天傍晚,11班的班长打完干草,让汽车连驾驶员老乡帮忙运回来。
驾驶员没有同意,这位班长趁他老乡睡着,把汽车钥匙“偷”了出来。
东北开车,晚上要放掉水箱里的水,不然第二天不能启动。
不会保养车辆的班长开着车,走了十来公里。
车因缺水烧坏了、抛锚在路上。
20多岁的小班长由于紧张、害怕、无助,索性把汽车停在原地,在忐忑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汽车兵突然发现自己的汽车丢了,如同“战士丢了枪”,属于重大事故。
11班班长自己交代了前后过程。
班长触犯了军纪,即将面临严重处分,官兵前去首长那里求情,也有一部分当地老百姓以“他还帮助地方修建过学校,帮助牧民收干草等”等理由前来说情。
军纪如山,铁令如山。
最终,11班班长还是被记大过处分,记录档案,终身携带。
虽然当时,铁道兵是工程部队不是一线的作战部队,但是毕竟是人民解放军,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
C
铁道是让人拾级而上的梯子
父亲说,后来他在铁路线上值守,特别是夜晚,从近处的灯光下,顺着铁路遥望远方,无限的铁轨正一点点地上升,而一个个枕木,恰是让人拾级而上的木阶。
京通铁路于1972年10月开工兴建,1977年12月4日全线铺轨通车,1980年5月1日正式建成交付运营。
历经8年,分为三个阶段:施工准备1年半,主体工程4年,配套工程2年半。
“1977年铁轨已经铺好,干的是配套工程,主要有铺石子、校正铁轨、信号设施等等。
”父亲回忆道。
筑路机平整后铺上铁轨,再铺上石子,用起道机把轨道从石子里抬出,用洋镐砸石头,最后对铁轨进行校正。
铺轨工作已经是半机械化了,而辅助工程却是人工一锤一镐地敲打出来的。
“比较苦的就是卸石子。
一列火车10-15个车厢,每个车厢装60吨,1个班约4-6人负责一个车厢,在2-3小时内卸完。
”
有一次,冬天来了一列火车石子,全连出动,外面大雪纷纷,寒风刺骨,他们几个小伙子从开始穿着棉袄,脱到夹袄,最后越干越有劲,越干越热,只穿一件单褂。
2-3个小时赤膊上阵,雪水、冰水夹杂着汗水,背上热气腾腾地冒着烟。
连队为了犒劳,晚上还加餐,喝了顿辣椒汤。
前期间歇性的水土不服,加上雪天卸车劳累、着凉,几个士兵都生病了。
父亲的肠胃也出现了问题,在部队诊所待了几天还不见好转,痢疾越来越严重,人越来越蔫,虚脱得抬不起头了。
后来,转到了野战军医院,悉心调养半月,父亲才恢复了元气。
生病平常事,也算是幸运的,而有些战友则长眠于那片草原。
东来站是京通铁路上仅有的两个用烈士命名的站名之一,源于1946年张东来在此地牺牲,村子改名东来村,车站后来叫东来站。
张东来牺牲整整30年后的1976年夏天,父亲和同乡战友汪永超、汪文灿从东来站赶往营地余粮堡吃午饭。
沙漠边缘温差也特别大,“早穿棉袄午穿纱”。
轨道车的后面挂着平板车,中间有1米多的一个缝隙。
平板车“平平的”,平到四面连个扶手、遮挡都没有,车上不能坐人,装着洋镐、铁锨、起道机等工具。
“汪文灿说他要坐到平板车上扶着工具去。
”父亲当时劝他,轨道车里安全,平板车危险。
汪文灿说那上面没遮挡反而更凉快。
车子没走多远,突然一个大的颠簸、晃动,汪文灿一下子被甩了出去,掉到两车之间的缝隙里,一米八的大个子瞬间就被平板车卷到车底……治疗一年多,最终没有保住性命。
汪文灿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
D
“铁道卫士”的士兵突击
今天,我从百度地图上查找,依然可以看到铁路中间的小路。
当年他们修路用的施工便道,已经变成了国道G111了,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开路人。
后来,值班守护铁道的日子到来了。
守护路段从余粮堡车站到西六方车站,大约10公里,父亲是老兵,他又带了2个新兵。
三人住在铁路旁的一个大房子里,房子有三间,一间是大炕、一间厨房、一间堆放工具物品及杂物。
屋后是大片大片的草地,他们三人打了压水井,浇地开荒种菜。
菜地丰收时,除了自足以外还反过来供应连队。
生活用品从驻地余粮堡用毛驴车运送,父亲当兵还学会了赶毛驴车这项技能,只是现在毛驴不见了,毛驴车几乎没有了。
周围有好几个村子,北边500米是小张家窝堡村,南边穿过铁路500米是胡家围子村,有临时的过道可通过,东边顺着铁路2公里有个常宝村,西边2公里靠近铁路远一点村庄叫宁家油坊。
除去“堡”、还有瓦房一村、瓦房二村、油坊等,标准的农耕生活。
父亲巡路以后时间比较宽裕,经常到各个村子里参与军民共建。
晚上可以追着电影队看电影,当时的电影有《英雄儿女》《地道战》。
不但有“油坊”还有酒坊,那一片村村都有酒坊,东北人在秋后用高粱、玉米等作物自己酿造“酒水”,是我们甘之如饴的粮食酒。
喝着粮食酒、吃着自己种的菜、晚上看看电影,父亲津津乐道了好多年。
父亲和他带的两个新兵,除去看守三间房子、看守铁路设施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巡道,巡查安全隐患、有人破坏等。
两个铁轨之间的交接处有严格的要求,不能有一张纸的缝隙。
有一次,一辆货车从远处驶来,声音率先通过铁轨传来,父亲突然发现了钢轨之间的有颗钉子松动了,本来就是试运营,各种条件都不完善。
货车过来,如果钢轨松动导致火车脱离轨道,会造成翻车的重大事故。
在万分紧急的时刻,父亲迅速找到旗子,远距离操作,让火车停到了安全距离之外,避免了一次事故,所以父亲还获得连营嘉奖。
往事如烟,可堪回首,他们的青春是闪过光的。
所以,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要保持一种蓬勃的生命张力,积极地迎接每一个晨曦。
不一定惊天动地,但是要丰富每一段旅程、丰盈下每天不甘寂寞的心。
落梅横笛已三更,草原深处征人行。
1980年,父亲退伍,“草原五班”生活也就结束了。
回家后第二年,1981年秋天,我出生后一两个月,父亲又找了一个在铁路上干活的机会。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位于祖国东西大动脉陇海线上,上世纪80年代,陇海线从单线扩展到双线。
父亲刚从铁道兵退伍,修过铁路,有经验、懂技术,被委以技术员。
干了几个月,当时的队伍去菏泽继续修铁路,负责人要把父亲带去当铁路工人,但家里人没同意。
父亲回家务农,彻底告别了铁路。
时光一晃,40年就过去了。
《铁道兵志在四方》中唱出了铁道兵“老铁”们的心声,“今天汗水下地,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同志们哪迈开大步朝前走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2019年9月23日,他们修建的京通铁路内燃机车牵引的铁路线路改建成了电力牵引,这是全国最大规模既有线路换梁施工工作。
同月,我履职中国铁建。
父亲参与修建的铁路迎来了新的时代;他的“老铁”生涯,也迎来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