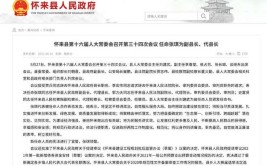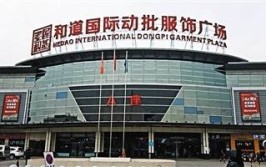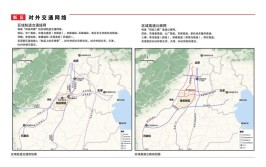那天住在了白沟河北岸的白沟新城。过白沟河,就是容城和雄县地界。
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雨,又是盛夏时节,白沟河里的水虽无奔腾咆哮之势,放眼望去,亦可观。
耳边仿佛响起元朝人刘因的句子: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又响起清朝人陆次云的句子:道出白沟河,沉吟唤奈何。古今陵谷变,高下战场多。厉鬼依残骨,耕人拾断戈。烽烟嗟又甚,搔首一悲歌。

就是这条河,就是这条曲折蜿蜒的河,今天在雄县城西和城南近乎划出一个直角,当地又叫大清河,一千多年前,其著名程度远超出今天人们想象,它做了两国的界河,河这边是大宋,河那边是大辽。
在空中俯瞰,它细若游丝。在现实社会,那时候,它就像一根时常绷紧的敏感的神经。
从现实,回到宋朝的雄州。
是的,宋朝的创建者,即显德六年(959年)随周世宗柴荣北征,率先抵达瓦桥关的赵匡胤。
瓦桥关设立雄州的第二年,大宋王朝在他手里诞生。一场意料之中的和平交接完成之后,他把柴荣未竟的北伐事业继承下来。
战争随之在宋辽之间展开。
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太宗赵光义再到宋真宗赵恒,两国交锋不断,互有胜负:
……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兵围瓦桥关,守将战死,宋军败退,辽精骑渡河追击至莫州。
至道元年(995年),辽兵夜袭雄州,知州何承矩出城与辽兵酣战,大败辽兵。
咸平三年(998年),辽兵侵,宋真宗赵恒亲征,至大名,辽兵闻而退……
何承矩此时业已出场。回到宋朝的雄州,最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就是何承矩。
2
史志中雄州相关记载。
何承矩,字正则,“河南”人。
何承矩的成长,得益于家庭教育,社会环境。
他的祖父何福进,历事后唐、后周,曾镇守真定。他的父亲何继筠,字化龙。在何福进精心培育下,何继筠很早步入仕途。
何福进死后,何继筠做过刺史,柴荣北伐,他全力配合。
入宋,何继筠以功不断获得升迁。赵匡胤对何继筠关怀至殷,五十一岁何继筠病逝,“帝亲临之,为之流涕”。
何继筠“深沉有智略,前后备边二十年,与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善揣边情,边人畏伏,多画像祠之”。可以说,何继筠很早就成了儿子何承矩的人生骄傲和学习榜样。
祖父和父亲均戎马一生,何承矩的起步,亦是由入伍锻炼,为棣州衙内指挥使始。不用父亲刻意地教什么,亦不用他刻意地学什么,跟随于父亲左右,见多了,他的视野和胆识,自然就宽了,大了。
父亲死后,何承矩相继做了闲厩使、崇仪使、知河南府。他在潭州任职六年,“囹圄屡空,诏嘉奖之”,政绩最为突出。
到河北之前,他还任过六宅使和潘州刺史。
到河北后,何承矩的第一个职务是节度副使。然而他的一道建议筑堤屯田的上疏,引起朝廷重视,宋太宗赵光义随即任命他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亲抓此事,“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3
务实,从实际出发,何承矩的实干精神很快得到回报、承认。淳化四年(993年),他调任沧州知州。
淳化五年(994年),转雄州知州,从此他真正与雄州结下不解之缘。
雄州地处边关前沿,他深知雄州对于朝廷的重要性,雄州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关系两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所以,到了雄州,首要的,仍是一切从实际说起,做起。他反复研究,精心设计,以喝酒赏蓼花之名,带僚属坐船实地考察周围淀泊,特意“作蓼花游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以此掩辽人耳目,在雄州达到“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的目的。他“推诚御众,同其甘苦,边民有告机事者,屏左右与之款接,无所猜忌,故契丹息,皆能前知”。
知于前,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何承矩式的智慧。但一场战斗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到任刚刚一年,至道元年(995年),数千契丹精骑夜袭雄州城下,伐鼓纵火,以逼楼堞。
他整兵出拒。
是的,没有悬念,雄州成了契丹人的梦魇,战斗以他的胜利告终。
可是,作为胜利者,他却不得不以胜利以外的原因离开雄州。
这是一次不太久的离开。
4
宋真宗赵恒即位,何承矩重回雄州。
赵恒开诚布公,告诉他:我嗣守鸿业,唯怀永固,思与华夷共臻富寿,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先帝继统之初,和好往来,礼币不绝,其后疆臣贪地,为国生事,信好不通,你任居边要,洞晓诗书,凡有事机,必能详究轻重之际,务在得中。
赵恒话里话外的意思全是和契丹人搞好关系,不想打仗。
这边皇帝这样想,那边皇帝可不这样想。他们不买账,咸平二年(999年),又发动了攻击。
咸平三年(1000年),赵恒想调何承矩进京任引进使,雄州百姓不放,“州民百余诣阙贡马,乞借留承矩”,赵恒亦被感动,诏书嘉奖,把他留下了。他于是借机再向赵恒建言“川渎泉源,因而广之,制为塘埭,自可息边患”;“慎择疆吏,出牧边民,厚之以俸禄,使悦其心,借之以威权,使严其令。然后深沟高垒,秣马厉兵,为战守之备”……
咸平五年(1002年),他兼领制置屯田使,想把停止了多年的榷场恢复起来,谋划着榷场开放,经济往来,互通有无,利益双方,亦有助于将两国的敌对状态化解于无形。朝廷亦批准了。然榷场才开,就因混入契丹特务,负责侦查的斥候卒在眼皮子底下被杀,关闭了。
事情还是想简单了。
现实环境是残酷无情的,在雄州的经验和教训提醒他:出发点再好,倘若不能通过现实的考验,时机不对,行之无效,都不能称之为好。
5
景德元年(1004年),不得不又一次离开雄州。
宋真宗赵恒说:“承矩读书好名,以才能自许,宜择善地处之”。
这年冬天,何承矩到了澶州。
就在这年冬天,宋辽订了澶渊之盟,和平之光悄然照在白沟河两岸。
第二年,即景德二年(1005年)的春天,何承矩又回到雄州知州任上。
边兵稍息,农政未修,景德三年(1006年),拜雄州团练使,随即又兼缘边安抚使。他听到赵恒“任边有功”的赞誉。
他已年过花甲。
他觉得一个六十一岁的疾病缠身的人,亦到该向雄州告别的时候了,雄州这样的国家要地,应该让更年轻有为的人来治理。
很早以前,肥乡人李沆和大名人王旦尚处卑微,以之“有公辅器”,他大加保举,后两人果不负其望。这一次,他向朝廷推荐了李允则——一个注定在他之后,像他一样,会将命运紧紧同雄州联系在一起的人。
他还有什么要说,要做呢?
可以放心走了。
他走了,到了朝廷安置他的齐州团练使任所,只七天,他就安详地走了。
听说消息的河北边民,“皆相率诣雄州,发哀饭僧”。那样的盛情、盛况,在雄州的历史,独树风操,刻骨铭心。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雄县新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年版。
(统筹/执笔 燕赵都市报 刘学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