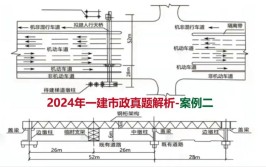扶风县的宏强,是我的战友。二十多年前我们在燕山里的小山沟里一起当兵。算起来他今年也快四十岁了。那时我们十七八岁,风华正茂。
部队里的战友来自天南海北,我西安他扶风,同是陕西人,同在一个连队,他当通讯员,我是文书,住一间房吃一锅饭,感情深厚。八十年代的后期,为了工作,为了转变人生,作为我们工农子弟当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那时的部队,尤其是山沟里的野战军,条件很差,我们一月拿十八元的津贴,吃着没有油的饭菜,半生不熟的馒头,我们扎根燕山,献身国防。
我们的部队是新四军六师的老底子,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功上孟良崮,击毙张灵普,抗美援朝守过上甘岭,唐山地震救灾等,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我们住的营房都是石头地基的苏式红砖瓦房。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为了北防苏联,从北京往北坐火车去看,经常能够看见那样的营房。据说这样的营区里住过东北军,也住过日本人,还住过苏联红军,可想有了多少年代了。冬天生火墙,当兵的住通铺,条件很差。我们去部队的时间正赶上部队营房改造,拆了老营房盖楼房,住了楼房有暖气,也不用睡大通铺了,当兵的都很高兴,高兴归高兴,但部队钱不多,当兵的都是好劳力,所以很多活都是我们这些当兵的自己干的。

宏强和我同年生,比我高,那时年轻帅气。在连队里做通讯员,按说通讯员和文书在部队里是比较舒服的。但我们连队是先进连队,领导抓的严,文书通讯员做完了自己的工作,照样参加训练,有活干活,有公差出公差,遇见训练演习,照样背电台线拐子去通讯保障。部队里搞营房建设我们照样和其他战士一样干体力活。宏强的手就是营房建设的时间伤的。记得那是夏天,团里把挖排水沟的任务给了我们连队,白天热我们晚上去干,我们两人也分了几米的工作量,拿着镐头,铁锹干了起来。别人分的地方都是硬土地,我们俩分的这段是沙土地,沙土比硬土好挖,我们暗暗高兴,我俩一定比他们完得快,早早的可以回去睡觉了。十二点的时间出了事情,我们的沟边垮了下来,把我们挖的沟半边都埋了。没有办法我们就把沙土又往外挑,干着干着,其他的战友都完成任务回营房睡觉了。工地上就剩了我们两个和头顶的照明灯。那夜,凉风习习,我们唱着歌,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就那样拼命的干。今天回忆起来,年轻真好,用不完的力气,艰苦的环境也阻挡不了乐观的情绪。
三点多钟我们的工作快完了,一个小小的石头露在沟边上,为了让排水沟平整好看。宏强用镐头撬了几下撬松了,用手试图把石头拉出来的时候,半面排水沟垮了下来,人是躲过去了,胳膊和手压在了石头下面。等我帮他把胳膊从石头下面拉出来的时候,食指和中指已经血肉模糊。那时我们当兵不到一年,害怕任务完不成领导骂,那样的情况下,还坚持把沟挖完才回到连队。由于没有及时清理伤口,宏强的手感染了。部队的医疗条件很差,反反复复大概一两个月才好,好了以后的食指就严重的弯曲变形,影响生活。从那以后他就老把那个伤残的手指圈起来不让人看到。
通讯员一般多是用新兵,给领导洗衣服打饭新兵好指挥。第二年来了新兵安排了新的通讯员,宏强就不在做通讯员,连里安排他去菜地种菜。菜地在营房的南的一道沟里,小汤头沟往里走,离营房的五六里的样子。今天想起来,那真是个好地方,两边都是山,巍巍的燕山绿葱葱的,山上有山里红,比卖的山楂小,但熟透的山里红酸甜酸甜的真好吃。有榛子,榛子是灌木,你很难发现,只有站的很近仔细去找才能发现,拨去外面的小叶子,刚摘的榛子是绿的,见了风一会颜色就变成了褐色的。雨后山间上有蘑菇,松树下面长的是松蘑,草丛里出的是草蘑,榛子树下的叫榛蘑。不训练的时间我们几个老乡就去宏强哪里去玩,采来山里红吃,采榛子,采了蘑菇用线穿起来挂在房檐下晾干。攒到了一定的数量把这些土特产寄给远方的父母。
宏强每隔一段时间就回连队一次,背走连队分给他的米面,有一个绑着绳子的啤酒瓶灌走分给他的菜油。他一个人住在菜地边得一个小房子里。自己做饭。那时我们都很羡慕那样的生活,不用训练,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不用听起床号熄灯号。过了许久我才明白,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呀,吃没有吃的,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白天看青山,晚上看星星。我明白了我们一去他为什么那么高兴,给我们做好吃吃的。我们最爱在哪里包饺子,菜地里有莲花白,我们把莲花白剁碎,把我们存的干蘑菇泡开也剁在里面,多放菜油,碎蘑菇鲜的跟肉一样,我们吃的饱饱的,傍晚我们上山,半山坡上有小溪在石头上冲了一个石窝,好似一个澡盆,我们在哪里洗澡,洗完澡浑浊的石窝第二天早上又变的清澈无比。有的时间宏强会搞一只鸡,或一只狗,我们杀鸡杀狗解馋。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和我们多见面,他用不穿的军装和老百姓换的鸡和狗。
菜地和房子修在河边,河是伊逊河的一个小小支流,从东面的五老图山脉上缓缓流下。平时水不多,枯水的季节就没有水了,军事地图上把他叫时令河。河滩边上可以开汽车。我老梦想什么时间要是水涨满了有多好看呀。
营房的大门岗白天是警卫连站岗,晚上是我们团直属队的通信连和机炮连轮班站,一个连队一个月,晚上也给我排哨,我喜欢站哨,一个人背着没有子弹的五六式步枪,对着黑漆漆的大山发发呆,练一会正步,心里默念着今晚的口令,一个小时一会就过去了,那是夏秋的一个夜晚,我二班哨。山里的雨说来就来,特大的暴雨,十点半开始下的,等我上哨的时间营门外山上下来水已经没过了膝盖。我马上下哨的时间看见一个黑影往营门来了,我下意识的提起了没有子弹的步枪,大声喊“口令”。那边喊“我是宏强”。等走近一看,原来是浑身湿透的宏强,头上还有血,原来大雨下的河水暴涨,淹了菜地,冲塌了看菜的房子,得亏年轻力壮才从废墟里跑了出来。
没有了菜地,菜是种不成了,宏强就在收发室里发报纸,发报纸没有前途,那年月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无非是城市兵安全混完三年回去有个工作,在有个党票就完美的很。农村兵就是有个党票也没有什么用,回去还是种地,农村兵要想出息,要不就是提干。那年月早已经过了苦干就可以提干的岁月,要想当干部必须考学,考学很难,文化和关系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工农子弟哪里有呀。在有就是转志愿兵,志愿兵都是有技术的,在我们通信连队转志愿兵就比步兵连里简单。正赶上我们连里有一个去学通信修理技师的名额,我们就打起了这个主意。动用了许都的关系,连里的,通讯股的,司令部的,能像的都想了,能求的都求了,几个战友的那点津贴结余都搭了进去。各种的艰辛今天想起了还很心酸,低三下四的,没有背景的人半个事真难,但总算是办成了,等有了技术,回来当了修理技师,离志愿兵就不远了,转了志愿兵当够了多少年转业了就可以安排工作,就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宏强在许多农村兵的羡慕中打背包去了军通讯团的集训队。这一去就是半年,中间我们去看了一次,我们去了军部旁边的避暑山庄,去了大佛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宏强回来的时侯白了,天天在室内学习的结果吧,也许是军直的伙食比步兵团好吧。连佩戴的军衔也比我们团里的好,那年部队刚刚改回军衔制不久,我们的军衔标志是尼龙线织得一个套,用线缝在老式军装的肩膀上,洗的次数多了就退色,而且缩水看着不是那么的平展。军直发了新式军装,肩膀上有套军衔的纽扣布带,套上就可以,并配发了新款军衔标致,新款军衔是绒布的,不退色也不缩水,看上去比我们的精神的多,宏强就戴着这样的军衔,我们好一番羡慕。谁问他要,他都不给,借也不行。那年我要探家,晚上我买了一瓶二锅头,一包榨菜,一瓶山楂罐头请他喝酒。他看着东西呵呵大笑“是不是要借我的军衔”我呵呵一笑。他啥话没有说连衣服脱给了我。我神气的穿着新军装新军衔回了趟家。到北京倒车,看见首都的兵穿的都是新军装和新军衔,这山沟里的部队就是比不上人家首都的兵呀。
转眼间三年到了。我们同年的城市兵基本都办了退伍手续。宏强没有走,我知道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奋斗下去,解决组织问题,奋斗志愿兵,实在不行找找关系把手上的伤评个残也行,听说评了军残回去也照顾个工作。走的那天我们穿着没有了军衔领花的军装,看着就像一群农民工。宏强把我送到车旁,递给我一个罐头瓶,里面满满的茶水,“路上喝”。从他的肩膀上卸下了那副无数人羡慕的新式中士军衔戴在了我没有军衔的肩上。许多的战友哭了,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今生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了,军人就是这样,我们来自天南海北,又回到天南海北去,我们的战友情鲜血铸就。我们俩没有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家离得很近,有机会再见的。
回了家其实还不如部队,部队里穿的一样,吃的一样,都那几个津贴。社会不一样,高低贵贱分的清楚,没有关系连个好工作也分不上。九十年代,工厂的效益差,工资发不齐,在下来砸三铁下岗都让我们这帮人遇上了,当我下岗没有饭吃在路边摆个小摊混生活的时间我挺后悔的,流血流汗换来的工作就这样没有了。
当我稍有点安定的时间去寻找宏强的时间,我们已经经不好联系了,我们退伍不久,部队换防去了天津和唐山一带,老的地址通讯不在了,那时间没有电话都是写信,宏强也许已经转了志愿兵了,我在心里祝福他。后来部队就全军换番号,我们的老部队换了什么番号,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后来裁军,整个集团军都裁掉了,那么长的历史,无数的战友,我我们连一个念想都没有了。
得到部队裁掉的消息我知道宏强也该回老家了。就照着记忆中他留给我的地址去了信,查无此人退回了。我的家也早搬了几次,留给他的地址不知道他还记着没有,我闲了的时间回回到原来的院子问问老邻居有没有我的信,一直没有消息。
有一年我回过一次原单位,门口看门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上个月有个人在单位门口打听我”宝鸡西府口音,好像姓徐,等了一上午。由于我下岗早,那么大的单位谁知道我呀。我知道是宏强来找我了,但就那样的错过了。我买了长途车票去了记忆中的通信地址和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扶风县卫生局,但还是一无所获,我时常认为也许有一天,不知道在城市的那个角落,我们会无意的重逢,他的那张笑脸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由于业务的关系扶风绛帐一带我也经常去了。打听了许多人,没有一点消息。社会发展到了信息时代突然有一天我的朋友说上网找不就行了,我半信半疑在扶风贴吧里发了贴,没有想到三天就找到了扶风的战友,赵红星,罗根昌,李雨汇等。但得到的消息是我最好的战友宏强已经因病于去年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不敢想象我们寻找了二十年就是这样一个永远不会再见的结局。红星战友给了我宏强家里的地址,可我真的没有勇气去看看,去看看他的坟头。我的一切记忆留在了二十年前,我要是不找多好,那样我还可以以为,也许一天,不知道在城市的那个角落,我们会无意的重逢,他的那张笑脸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我该说什么,人就是这么的脆弱,一声再见很简单,许许多多的人一声再见,永远都见不着了。
如果有来世我们还一起当兵,做战友,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宏强战友,安息。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西安的战友祝你节日快乐。
文/家住未央
图/来源于网络,感谢拍照战友家住未央
2009年8月1日(初稿)
2021年12月29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