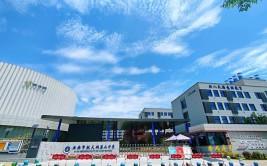1985年,平运司传统的宝鸡上站煤运输业务已被省际行业竞争冲垮造成的货源紧缺已经两年多时间了。84年的援藏工作结束后,各车队都在四路出击,寻找货源。二队因为被改编为客车队,公司把40余辆解放牌货车移交五队,同时决定对这批老旧车辆的汽油发动机进行玉溪柴油机的更换,以提高动力性和降低营运成本,大约每周更换一台。
我刚刚从老同学刘德平手中接过来的114号车因为才大修过,被安排在最后更换,我便随着这些已经更换了发动机功率变大了的柴油车奔赴车队新的货源基地——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的十多个林场里执行运输任务。
四月初来到迭部县,深沟山区里各林场采伐区的冰雪还没有消,无法进山拉运木料,但临近公路的供销社和村寨里平时积存的扫帚和板材等物资还可以拉运到周边的农业区,这里的扫帚外销量很大,就是用熊猫吃的那种箭竹制作的,它比我们关山里出产的扫帚更长,比秦岭山上产的那种粗竹子制作的扫帚柔韧性更好,很受陕甘宁农村人们的欢迎,那时候碾场扫院都需要它。这样的运输业务一直持续到五月份山里蕨菜长成的时候,我们又接着往兰州、定西的外贸部门运送盐渍蕨菜,这里的蕨菜又肥又大质量好,是向日本等国出口换汇的产品。

每到蕨菜采摘期,外贸部门就会组织人员大量收购,他们雇人把水泥和红砖抬上山腰,砌一个用盐水腌菜的池子,盐渍后的蕨菜可以保鲜,待蕨菜积存到能装车的数量时,再用一百公斤装的塑料桶把盐水和蕨菜一起封装后弄下山来运走。据说运到外贸加工厂后还要脱盐、烘干才能出口。而山里蕨菜的采摘期只有二十多天,一位强壮的村民每天能采摘一、二百斤,每斤四毛钱,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但也很辛苦,因为山林里蕨菜分布也不均匀,他们攀高爬低,远近不一。
听说前一年发生过火灾的地方蕨菜非常好。拉运这种货物很省力,不用捆绳,不走山道。但车队分配的运输木料任务很快就来了,因为山里的路通了。六月份开始,车辆转入各个国营林场木料的转运业务,车队在迭部县第二旅社驻地办起大灶和修理部,方便驾驶员的生活和车辆保养,每次返回驻地时,能吃到家乡味道的饸饹面、羊肉泡也非常惬意啊。看到近年来网上的这幅旅游示意图,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些地名标示的地点当时都是当年各林场的名称:多儿沟、花园沟、水沟、旺藏沟、阿夏沟、尼傲沟、腊子口……
最令人难忘还是那个益哇沟,当年在这条沟里拉运果园专用支撑果树的架杆,必须先上山,在半山上的山坳里装载木料,这种材料在林场里规范的名称叫做“小径木”,即大头只有十几公分、长度最长的十四、五米,而解放车的车厢长度只有四米二,驾驶室顶上伸出去两三米,后车厢又抻出两三米,整个汽车就是一个活动的木垛,又像是一个巨大的“刺猬”。在这里只有上山的道路,而下山路却是起起伏伏的一条五、六公里长的泥浆槽,车行其中既不用变速、也不用刹车,轻轻扶着方向盘顺着泥槽溜下这段没有大弯道的山沟就行——这让我这个成年人在这里着实体验了一把儿童们玩滑滑梯的感觉,既惊险刺激,又觉得不可思议!
如今,在这条沟的村寨里开发了著名的“扎嘎那”景点。后西藏村是多儿沟林场最深处新开发的一个采伐区,临近四川省的地界,这里木料多,派进去的车辆也多,新修的道路翻浆严重,每次只能拉半车木料出来卸在公社旁边的老公路上,再一次进去拉半车木料出来合成一车,如此往返三十公里。这一带距离迭部县城近百公里,靠近东边的舟曲县,老百姓半农半牧,都能说汉话,我们的吃住问题容易解决。一位喇嘛跟着我进沟给寺院里捎带柴火(就是砍伐过程中产生的不成形木料),他很健谈,说他们这里没有建立林场时风调雨顺,粮食年年丰收,人口多,孩子多,就叫多儿沟。
自从有了林场、来了汽车之后,暴雨雷电越来越多,泥石流、洪水频发,粮食也不好好长了,“我恨你们,你们给寨子里带来了灾祸,尤其是那些电线杆上常常闪光冒烟,冒犯了山神,引燃了山林……”我想,这老喇嘛所说的“恨你们”是指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而言,话说对了多一半,却又理解错了电线杆。那时候,山沟里与县城的交通不便,几十公里走出沟口才能到达搭乘甘川公路上的班车站点,我们去了以后,就可以把他们捎到县城或者沟口,有一位在迭部县政协任职的活佛就坐过我的车到县城开会,他坐在驾驶室里虽然没有说话,但一路的几个检查站都对我摆动绿旗放行,没有一次排队等候,原来是他的随同人员把一条金黄色的哈达飘在了车窗外面,算是一个特殊标志吧。
我这次拉运的是多儿沟公社木材加工厂交给县林业局木材加工厂的原料,林业局检查站平时队这种木料检查十分严格,谨防他们挈带林业局特批才能出售的柏木棺板材料等。与在迭部县林业局工作的静宁老乡苏女士认识后,她常常给我们一些特殊货源,六月份,他们要了两台车去西边200多公里外的碌曲县双河镇苗圃拉运树苗,给旺藏沟和达拉沟的林场恢复残次地林的人工种植。
我和同事郑全玉承担了这项任务,路途中经过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管辖的一个村寨会车时,汽车的右前轮不慎陷入村民占路开垦的菜窐里上不来,而他家的两只大狗又“汪汪”不停地狂叫,走在后面的郑全玉师傅迅速连接钢丝绳把我拽了出来,我俩逃之夭夭,后视镜里看到有一伙村民在那里又跳又喊,好像是在诅咒我们。
记得还有一次与王琢在若尔盖县林业局管理的一个林场装料,重车行驶中,被一伙手持经幡木杆的村民横路拦挡,他们要去敬山神,我见人太多,便假意要靠边停车,却在他们让开后一脚油门冲出了阻拦,往前走就上山。但走在后面的王琢却被拦了下来,我在盘山路上看到他车上坐上去了三十多个人、还有许多木杆,王琢气的蹲在一边,这车那么重,明显是起不了步的。我只好停下,招呼他们分一半人过来,坐我的车一起走。
同在白龙江沿线的甘川公路(后来的213国道)旁边,甘肃藏族和四川藏族的村民的民风有着巨大的差异,甘肃这边老实本分,普遍通汉语,容易沟通;四川那边接近牧区,语言不通,给人横蛮难交的印象。据说甘肃这边过去属于杨土司杨积庆管理,这位藏族首领的祖上在明代时就归顺了朝廷,并要求皇帝赐姓他家姓杨,他决心效法历史上杨家将那样效忠朝廷,所以在甘南几乎所有藏族具有汉族姓氏的人家都姓杨。他们的习俗是头领姓什么,部落里民众就跟着姓什么。杨土司在红军长征经过甘南地区时帮助过共产党,后被国民党军阀鲁大昌派人杀害,解放后杨积庆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他的子孙多人在甘肃省或甘南州政协、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而鲁大昌就是1935年在腊子口与红军打过恶仗的那位国民党时代的“陇南王”。
拉运树苗那次,到达碌曲县双河镇时,街道上有人呼喊我们,并追随我们的车一起进入苗圃,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供销社工作的庆阳人赵女士,她说自来到这里十多年就没有见到过陇东老乡,在街上看到平凉车时就激动不已,一路追了过来……她一定要邀请我们去她的单位坐坐。在她的宿舍里,她指派一名藏族小伙提来一壶熬得红艳艳的“大茶”,说是用来搅拌酥油糌粑的,只见她拿出土红色的木碗,取出装在牛皮包裹着的桦树皮桶里的青稞面和酥拉运树苗那次,到达碌曲县双河镇时,街道上有人呼喊我们,并追随我们的车一起进入苗圃,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供销社工作的庆阳人赵女士,她说自来到这里十多年就没有见到过陇东老乡,在街上看到平凉车时就激动不已,一路追了过来……
她一定要邀请我们去她的单位坐坐。在她的宿舍里,她指派一名藏族小伙提来一壶熬得红艳艳的“大茶”,说是用来搅拌酥油糌粑的,只见她拿出土红色的木碗,取出装在牛皮包裹着的桦树皮桶里的青稞面和酥油、拌了白糖,用“大茶”和面,捏成面疙瘩递给我们,说“这就是藏族人待客最高级的糌粑。”其实我俩都去过西藏,喝过酥油茶,糌粑却没有吃过,拿过来闻了闻,还是很腥,她看我俩迟疑,便说“这东西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尝一口试试”,用牙尖刮了一点,嗯,很香甜!
活像我们吃的月饼馅儿,那腥味儿来自酥油,是牛奶里提取的油脂,外国人吃的“黄油面包”里的黄油就是这东西,藏族人吃喝用它,点灯也用它,甚至敬神的时候也要把它抹在神龛和石碑上……聊了一会儿风土人情后,她带我们去供销社商店里转转,她指着一堆装着的树枝、树叶混合物的草袋子说“这就是咱们刚才喝过的大茶,其实是南方茶农们修剪茶树时剪下来的树枝树叶,而藏区的人们把这东西熬制两三天了还在用来冲酥油茶,还说这是最地道的吃食……”说到藏语里的地名,她还解释道:碌曲是藏语“青色河流”之意,汉语就是洮河,玛曲是黄河、那曲是黑河,舟曲是 “白水河”,汉语就是白龙江,因为白龙江的水是“开山水”,即水流湍急,水石激荡,石头的粉末把江水都染成白色的了……
这边老乡们聊天叙话,那边苗圃里吆喝着装车,每车装了十几万棵杉树苗。我们平时都认为从那边拉过来的是松树木料,其实都是杉木(有冷杉和银杉之分),一年生的树苗如同银针、三年生的就像筷子、五年、七年生的像指头粗细时才可以移植栽种,苗圃里大片的苗木都被黑色尼龙网遮盖保护着生长,高原地区植树造林真是不易呀。拉运树苗和拉运蔬菜一样,装车后就得连夜不停的走,尽快送到地点卸车,以免树苗发烧,失去活力。
往回赶的路上又来到若尔盖县的辖区,这里是牧区路段,没有被牧民纠缠却被几个穿着脏兮兮小藏袍的小屁孩儿袭击了,他们站在路畔嬉笑着等待汽车过来,冷不防他们向车窗里打进来什么东西就跑了,急忙停车查看,原来是两棵曼陀罗的果实,正好黏在车窗撑举架上的擦汗毛巾上,好险啊,这种满是尖刺的家伙打到眼睛上可咋办?回到车队和同事们谈起这些事儿时,大家都说“那地方还没解放,路过时必须小心,别开窗户!
”我们去合作市、去兰州市都要经过那里。
如今若尔盖那边的旅游业也很红火。两车树苗分别在多个山坡地点卸载,林场里往年种植的人工林长势很不错,而没有恢复造林的那些残次林地巨石裸露、草木稀疏,沟壑被山洪冲刷的非常严重。达拉沟很深,向南走到头就是甘川边界上的俄界村,那里是红军长征路线上一个很重要的“俄界会议”发生地,那时候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分裂路线严重斗争的时期。中央红军走出达拉沟和旺藏沟,在沟口的旺藏寺和次日那村寨住了十几天,筹备了足够的粮食才决定打开腊子口,冲出甘南进入岷县继续北上来到黄土高原的通渭、会宁、静宁到六盘山一线的。
这段故事写在早年看过的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里,书里写到:红军在旺藏寺暂住的时候,喇嘛们和村民们都跑进山里去了,战士们发现寺院仓库里的粮食很多,他们就留下了银元和借条,装走了等量的粮食,毛主席还夸奖这里的萝卜长得像牛头一样大……几个胆大一点的村民回家偷看红军时,发现他们并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红头发像魔鬼一样,这才动员在山里老乡们返回村寨。近年来的资料里讲,当年是杨土司杨积庆下令不准藏民抵抗红军,不锁家门、放开仓库,让红军安全通过就行。第二年,红二、四方面军路过甘南时,更是与藏民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如今在甘南各县的红色旅游的景点非常多。
腊子口,是甘南最著名红色旅游景点,因为这里曾经是红军长征路上的“腊子口战斗”发生地。当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到这里时,却被巨大的铁尺梁横亘在眼前,如果不能突破就走不出困境。萧华将军在《长征组歌》里写到:“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骑,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建立根据地……”
当年杨成武将军带领红军冒着枪林弹雨打开了国民党军阀的围堵,几位苗族战士用绑腿的带子结成绳索爬上了敌军阵地的上方,用石头砸退了鲁大昌的“机枪营”,红军胜利翻过旁边的大山到达宕昌县的哈达铺,毛主席和战友们在那里确定了去陕北发展革命事业的路线。而我们在这里跑运输,面临的也是铁尺梁这座大山,林区里出来的重车从舟曲与迭部交界处的代古寺到铁尺梁一路向北上坡,特别是从腊子口开始爬坡到山顶这11公里,俗称“十八弯”,比西兰公路的六盘山高出了两倍 !
我们五队改造的柴油发动机解放车一开始来这里时由于动力强劲,重车一路突飞猛进,惊艳了众多的沿途的同行,那时候,这一路上跑的最多的还是兰州、甘南、武都、定西运输公司的车辆,他们常常羡慕的说,一听到柴油机声音,就得急忙给你们让道,有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你们超车了……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玉溪柴油发动机与老解放车的传动系统不配套,驾驶和保养方法必须改弦更张,但驾驶员这方面的谨慎习惯还没有养成,造成车辆路途损坏的情况越来越多,不是损坏差速器,就是扭断传动轴,“大牛拉小车”的问题开始凸显了,一路上“卧轿”被救急的车辆都是我们五队的。要说这种更换柴油机的车辆,如果能按照正确的使用规范驾驶和保养,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五队改制的60辆老解放车硕果仅存的就是转业军人刘效春师傅在公司改制时买走的那辆292,他严格遵守操作规范、精心保养,一直把车使用到报废年限。而其他车辆都在时代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仅仅用了一年多就报废了,因为玉溪柴油机厂更新产品不再生产这种配件了,这种环境就没有留给我们驾驶员试错的机会,他们只好重新换上汽油发动机凑合下去。
在当年货源紧缺的情况下,五队来到迭部县,让我们驾驶员有了不同平日的感受,在拉运上站煤的宝平公路上,我们像是摆摊的贩子,求着路人购买我们的货色,曾多次遭遇带着拖车被派去宝鸡拉粮、拉化肥而苦苦等待十几天又被空放而返的困境。而在迭部林区,往往是货主求着我们给他运货,自我开车以来,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台班费”的概念,即雇车后因故没有装货耽误了运输的时间必须一天付费120元。五队在迭部运输业务不错,常常还有“利装”,即往返货物,往北方向给陇西、定西和陕甘宁地区送货返程时还可以捎回给林区各个建设工地的陇西文峰镇的砖瓦。
当地藏民家里都有自留山、自留林,他们一有机会机会就会拦车要求拉运他们家里的檩条、椽子去兰州、临洮甚至更远的地方售卖,一次我的车被雇拉着木料去定西,结果他们联系到的收货人变卦不要了,他们便收取了违约金又去了古浪县,所谓“违约金”就是用一副石头眼镜顶账,价值大约三百元;还有一车拉到秦安县莲花城的檩条,由于他们电话中联系时口音不同,把“配件厂”听成了“皮件厂”,导致两天里找不到皮件厂和收货人,那时农村地方通讯条件差,只好把这车材料贱卖给了路边的煤贩子,那时候农村正在大兴土木,建造房舍,一根价值百元的檩条被折价一半啊。这些售卖自家木料的人家里我也去过,家里很穷,但他们一旦拿到木料钱便在兰州的旅馆里大肆挥霍,吃光化尽才回家。
我也遇到过马明信这样诚信可敬的货主,他是漳县的回族人,也做着把林区木料贩运到周边地区的生意。一次去临洮卸货,当地村民见木料品相好,便群起抢购,居然把材料哄抬到很高的价码,我见状便帮腔说:“准事”,老马却在收款时退给了买主一部分货款,他说:这些老百姓看走了眼,这些板材看起来很好,但其实都是“站干木”(即死树),不耐年程。咱不能昧了良心了挣钱。这人的信仰非常虔诚,每到下午四点礼拜时候,都要求我停车,跪在路边祷告一会儿。他在这一路沿途人缘很好,我们以往在经过木寨岭、白杨林地段常常被人盗走车上的物品,备胎或者篷布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当我讲起这些烦心的事儿时,他安慰我说,咱们这次返回就去找找那村里的熟人。之后通过熟人沟通,我被带到到山沟里一个隐蔽的特大草棚里,好家伙!
这里居然比我们车队料库的东西还多,轮胎、篷布、大绳、防滑链条、油桶、千斤顶等等,花了三十元的赎金找到了前段时间刚刚丢失的篷布,因为上面印着车号也好找,同时又捎带给王琢找到了丢失的备胎,花了五十元的赎金交给看管草棚的哑巴老头,他便让另一位“半蔫汉”(智障人)推着板车帮我把这两样东西送到了我的车上。
白杨林,这个村子地处木寨岭南坡下面,虽然是个草山但没有树木,老百姓烧柴极其困难。有了这次进村办事的经历,我逐渐与这个村子的村民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原来以为“他们都是贼”的印象也渐渐地淡化了。我们每次送完木料返回迭部县的时候,经常是空车或者拉运装载不太高的砖瓦,经过漳县大草滩的时候就在那里购买一些当地村民捆扎好、晾干了的的柴火捎给他们,一捆大约(约五六十斤)三元钱。我每次代买的柴火总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后来那些以前不敢在这里停车的同事们也加入了帮助老百姓的行列。自那以后,我们公司车队的车再也没有丢失过东西。以前如果汽车在这里发生了故障,就只能迅速的把车拖走,如果你在那里暂停一会儿,防不住就会被人拿走东西或者扯断电线或绳索,找他们理论时又会招来一大帮起哄的村民……
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啊!
说到民族团结,让我记忆犹深的是舟曲县洛大公社卫生院的杨大夫。他是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毕业生,在卫生院是个多面手的医生,既是内外科主任,又是X透视机操作者。我是在一次去武都万象洞送货途中突发严重感冒去卫生所看病时认识他的,他给我推了静脉针,顺利完成任务后,我从武都返回时给他家带来了新鲜水果和蔬菜。这样一来二去,在这条线上我和同事们就有了一个“保健基地”。
杨大夫是文史爱好者,我也喜欢说古道今,我俩谈天说地,总有说不完的话头。洛大公社地处白龙江畔,白龙江畔的公路常常发生塌方、滑坡,有一次我们几辆车被堵在洛大公社不远的地方回不了迭部驻地,只好投奔卫生院的杨大夫。雨淅淅沥沥下了好几天,我们就在寨子里呆着,在杨大夫的家里住宿吃饭,他家饭食与我们家里大致一样,但还是有两名同事不习惯,耐不住寂寞,他们返回武都方向绕道天水回了平凉。
而我在寨子里被村民们在大雨间歇的空挡时间里叫上山坡,去给他们正在修建的喇嘛寺工地上拉一些石块,在那之前,他们都是把石头从山上背下来的。在已经建成的神殿里有两位庆阳合水县的画工正在给神像描金绘彩。这样,我就又多了两个聊天的伙伴,喇嘛和村民们也非常敬重我们三个帮他们修建寺院的汉族人,给我们供吃供喝,关怀有加。七、八天后,塌方路段被修通了,当我返回迭部县驻地时,车队领导们大吃一惊:“这些天你去了那里?害的我们打电话到处找你!
”……
两年后我在安口特意找了一车运给舟曲县毕节供销社的瓷器,打算顺道去看望一下老朋友杨大夫一家,可不料在岷县汽车站就遇到了他们,我见杨大夫很瘦,还咳嗽得厉害,他们要去兰州看病,我便背地里问他的儿子海龙咋回事儿,他说“阿爸可能是……”
我明白了,杨大夫一直在使用那台老掉牙的X光透视机,高强度辐射可能是他得病的原因。谁能想到,此一见居然是与这位老友的天人之别了……
再说那次回到迭部车队驻地后,领导们要我详细说明这次出车后那么长时间不见返回的原因,原来这次任务是车队派我给某某沟林场的职工们为其在武都的家乡拉一车烧材(林场里采伐过程中摔坏的木料),谁知他们是打着拉烧材的幌子,把一大盘两吨多重的钢丝绳装在了烧材的下面,这钢丝绳是林场从山里运输木料的绞车上报废下来的,听说丢弃在山里好长时间了,但国家的财产不能私卖,而这些职工的家乡搞旅游开发要建一个过江的钢丝吊桥正好需要它,所以他们就在深夜里把钢丝绳盘在了我的车厢里,十几个人连拉带拽,用时三个多小时,出发的时候都快到凌晨五点了,我一夜在等候在车上被冻感冒,凑合到洛大公社就去找卫生院才遇到杨大夫的……
那座桥修好后存在了多年,就是武都汉王镇的万象洞门口白龙江上的那座桥,遗憾的是,我至今也没有参观过那里。在甘南还有一件挺让我感动的往事儿,话说一次从岷县给临潭县农机厂拉了一车废旧金属材料,临走时采购员介绍了两名藏族人搭便车,一路上他俩用藏语说说话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便打趣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年龄大的回答说叫“捏次力”,年龄小的说自己在学校的老师给他起了名字叫“勒宝”,我便开玩笑说要给他们起个汉人名字,他们很高兴,我说你就叫“年慈仁”吧,并且解释了名字的含义,还说有一位副省长也姓年,另一位直接就叫“李宝”好了,他们越加兴奋了,摆动着宽大的袖子一再表示感谢,却把我的变速杆套进了袖子里,恰好这时候急上坡需要“抢挡”( 就是连续降低挡位),搞得我一时找不到变速杆,错过了最佳操作时机,陡坡上猛抬离合器踏板,“啃噔”一下扭断了传动轴的伸缩叉,无奈,只好踩着刹车把车倒滑至平地上,我便急忙拦车去五十公里外的岷县购买伸缩叉,让他俩给我看车。买上配件后却又找不到能返回故障车地点的车辆,眼看天就就要黑了,几乎没有过往车辆了……只好就地住宿,这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担心的是这么冷的天,临行怎么就没有交代他们把机器里的水放掉?如果发动机冻坏了可咋整?
第二天天不亮就去车站买车票,十点多赶到车跟前时,我立刻喜出望外!
——他们昨晚不但放掉了发动机里的水,而现在又去附近村子里的亲戚家担了两桶热水让我启动发动机!
我在庆幸自己好运,也在这样想,是不是我帮助藏族同胞修庙得来的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