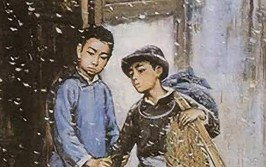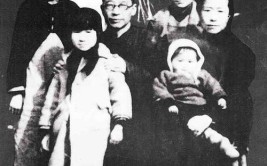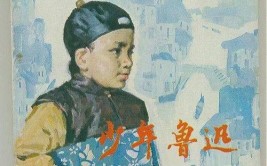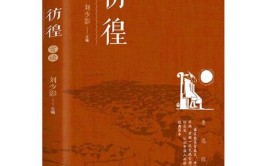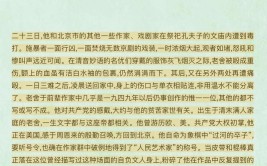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已经不用太纷杂地思考,自大二以来,我的主要阅读和研习都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尤其对鲁迅和老舍先生的作品与历史研究文献阅读较多,当然在这里选择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苏庆昌先生,他和王惠云先生一直是国内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俩人合撰的《老舍评传》是老舍研究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在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苏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老舍研究方面的课题,“题目尽可能地小一些具体一些,可以小题大做,不能人云亦云。”这是苏先生对我的论文选题提出的基本要求,我颇以为然。
老舍先生的小说作品从早期的《老张的哲学》,到代表作《骆驼祥子》,再到后期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反映了旧时代北平下层市民社会的形形色色,小人物的苦难命运、曲折挣扎,研究的具体题目仍然很多,一些问题也不是一篇本科学位论文能够承载的。思来想去,最终确定了一个小小的题目:老舍小说的写景艺术,题目虽小,却也没有人针对此问题做过研究,驾驭起来没有太大的难度。苏先生同意我的想法,“把对老舍小说风景画的研究与风俗画结合起来,因为这是老舍小说的一个特色。同时要选择现代文学作家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更显著地说清老舍小说写景的风格特色、艺术旨趣。”其实从大二以来就不断地和苏先生接触,有的时候在校园,有的时候去家里,从来很少聊过什么闲篇,难得一见的瞬间,总是有无数的问题、困惑,希望从先生那里得到答案、启发或思路引导。苏先生也总是谦逊包容,谈笑风生的,哪怕我的问题十分浅显和幼稚。
那些日子,一遍遍地翻阅老舍原著,搜集资料,整理卡片,梳理思路,反复权衡,最终洋洋洒洒地写了万余言,又在先生的指导下反复修改,努力认真对待着每一步每一个细节。苏先生了解我的进程,也了解我的态度,最终认真评阅后给论文打了“优秀”,而且推荐了当年的“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并推荐发表在当时的《河北师院学报》上。一个人在青春追梦的岁月,又一次得遇春风化雨、点亮心灯并引路前行的先生,真是三生造化。

毕业实习还在前面等候。虽说学习了四年,但是从未登过讲台,不知道站在台上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镇定自若?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丢丑败兴?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那将是又一次更艰难地跋涉前行。
我们一行八条汉子被分配到了晋县二中。又是二中,从学生到当老师我怎么从来没进过一中呢,真是小小的命运玩笑了。带队的指导老师是现代文学组的封连发老师,一个沉稳严谨又大刀阔斧的老师。我们毕业后封老师就离开了河北师院,在时代的浪潮催动下下海经商,后来成了石家庄市电镀厂厂长,是那个时代呼唤而出的开拓进取的弄潮儿。
毕业实习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两个人一组。我和邱树林分在了一起,他是一个写字、画画儿、吹笛子萨克斯的艺术才子,后来曾任河北师大艺术设计学院副书记、工会主席。实习期间虽说每个人也就讲四五篇课文,对于我这个二十郎当的年轻人来说仍然挑战性极大,况且我遇到的第一篇课文就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上高中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作家之一应属鲁迅先生,为什么?因为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半文半白,语言简练锋利,加其思想博大精深,复杂难懂,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当时的中学课本里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等一大堆鲁迅先生的文章,尽管认真苦学,也是一知半解。上大学后,随着对现代文学的广泛阅读,特别是对鲁迅著作的阅读与研习,才算慢慢走进鲁迅先生的思想世界,也理解了自己中学时的苦恼心境。也不是我自己不懂,那个被著名现代文学专家王晓明先生称作“中国现代最苦痛的灵魂”的鲁迅先生,为了民族的觉醒和塑造崭新的国民性,其精神之坚韧,思想之博大精深,情感之冷酷深情,斗士般之疾行果决,岂是轻易能懂的。在大学直到今天,鲁迅先生一直是我最喜欢最尊重的作家。
我像钉子一样坐在办公桌前和凳子上,那段日子真的是除了吃饭睡觉,脑海里只有一件事,研究鲁迅,反复体会《记念刘和珍君》文章里的每一个语气,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认真设计教案里的每一个讲解方式、节奏把握甚至态势语言。一个人对着墙角反复地讲认真地讲,像上了讲台一样地讲,主动邀请封老师听我的试讲,针对问题一点点地改正,直到人都要讲吐了,讲的宿舍里所有人都认为我魔怔了。
我镇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几根粉笔、教案和教科书,背诵着课文给同学们讲完了第一课,下课了,高一班里的同学们给出了热烈的掌声。我知道,我已开始走出那段忐忑不安的泥泞。
一份跋涉一份希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后来封老师跟很多人讲过,学军是个当老师的好材料。我获得了优异的毕业实习成绩。
毕业分配在即,那时的大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机巧心,纯粹单纯的可爱,像那时田野里纯净的白雪。服从分配,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是多数人心中的想法。年级里的好几名同学直接申请去了西藏、新疆和青海,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一学期时,班主任吴桐庆老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有两个名额,你准备好去当兵。”不是在开玩笑,吴老师以一个老军人的老辣眼光,一定是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那时对越自卫还击战已经到了尾声,但前线依然不时有战事发生,当时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从军,在军校学习两个月就要到前线去,我真的可能当兵去前线吗?一想起这些,内心还真莫名地兴奋了一阵儿,但最终年级里只有一个名额,班里的体委李俊峰去参加了海军,他是体操运动员出身,浑身上下的腱子肉。
我最终被留在了中文系,在系里开始教书和继续学习,直到九四年的夏天。
风风雨雨四年,热热闹闹四年,辛苦跋涉四年,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泥泞路,终于毕业了,当然是该欣喜的。同学们走向四面八方,我一个个地为同学们送行。一个午后,当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曾经那么多打打闹闹的身影都已远去,偌大的男生宿舍里已经剩下我一个人。那一瞬间,无边的惆怅孤单大肆侵入我的内心,眼泪簌簌地流淌下来,像一人看守着钢七连宿舍的许三多。
人生是一场艰难且长程的跋涉,会有风和日丽的平坦路,更会有雨雪纷飞泥泞难行。大学毕业了,每个人更远更难的跋涉也就开始了,可能还注定是一个人的彷徨漂泊无助前行!
还好我刚刚二十岁,那时正值炙热的八四年七月,时代的春潮正浩荡而来,在这个校园在这个城市在未来的漫漫人生,我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完)
作者简介:张学军,1964年5月生,廊坊市固安县东位村人,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写作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写作学。1994年调任广告传播系,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品牌营销、传播与广告实务。出版著作有《写作智慧论》(主编)、《中国酒业营销思想库》(四卷本,主编)、《六个核桃凭什么从0过100亿》(专著)、《把品牌建在顾客心理》(专著)等,发表专业论文多篇。为十八酒坊、六个核桃等著名品牌创始人,并担任多家快消品企业品牌与营销顾问,曾获中国酒业金爵奖十大策划人,中国食品业金牌策划人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