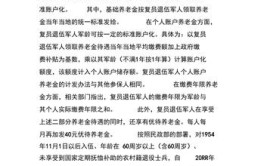当他微颤的右手缓缓举起的时候,我想:这是他最后一个军礼吗?不!
这只是他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向党的事业表示的又一次忠诚……
------摘自这次行军结束后的日记

尽管三月的天气还很寒冷,可我却急得浑身燥热。对着在迷濛的晨雾里提着自己的行李争先恐后上车的退伍老兵们,我连喊了几声:“站好队!
点名!
按次序上!
”但不知是骤起的风把我的声音淹没了,还是老兵们认为摘了领章帽徽就失去了约束,不但他们毫无反应,连我自己都感到这声音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我不禁暗暗恨自己:如果早当两年兵,职务再高一级也好哇!
可我七五年入伍,当兵还不满三年,现任参谋。更可恼的是我还姓“傅”,不了解的人一听,嘿,连参谋还是个“副”的。凭这些条件,要送这十六名当兵五、六年的老兵安全返回原籍,而且还是单车前往,我能压得住轴吗?……
“算喽,副参谋同志,别那么正规啦!
这人们站了五六年队还没站够哇,喂,没来的举手!
”
又是魏成!
从清晨四点半至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他戗了我好几次了。而且这回“副参谋同志”喊得格外刺耳。压了几次的火气这会儿猛撞到头顶,我正要发作,突然,一只大手攥住了我的胳膊,紧接着传来低低的声音:
“我数过了,十六个人一个不少。别上下折腾了。”说着,我的胳膊被使劲按了一下。
这用力的一按像是落下的气锤,把我冒出来的火气砸了回去。虽然天还没有大亮,看不清人的面孔,但我知道,这是耿志。对呵,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对象呵,还这么呆板、这么大火气!
我冷静下来,默默地走向车尾,扒着车厢板仔细清点了一番。也怪,乱哄哄的吵嚷声渐渐平息了。我心里踏实了几分,一股感激之情使我又想到了耿志 。是呵,同行的还有我的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指导员嘛。
我入伍就在八连。那时,耿志已经是任职四年的老指导员了。他身材中等,脸庞黑瘦,下巴上有一块显眼的伤疤。乍一看,像四十出头的年纪,实际上那一年他才三十三岁。记得下连不久,我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天晚上,耿指导员叫我去散步。我们沿着河边长满垂柳的堤坝慢慢地走着,边走边谈家常……我这才知道,解放前他在家讨过饭,尝遍了方圆几十里地所有能看到的树叶子。我有些不相信,在一棵粗大的柳树下,信手捋下一把树叶,指着那叶片上的小绿豆豆问他能不能吃?他微微一笑:“没办法的时候也得吃呀,不过又苦又涩。那小豆豆里面,个个都有虫子哩。我就是上树采它,头一昏掉下来,落下了脸上这个疤。”我连着掰开几个小豆豆,果然每个里面都寄生着一条小虫。我惊讶地望着他,只见他摸着下巴上的伤疤,沉吟着说:“要不是有党,这宝贝怕是要吃到现在哩……”
那一夜,小豆豆里面的虫子和他下巴上的伤疤,总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我久久没能入睡……
七六年初,我调到连部当通信员。不久,有人来连队帮助批什么“翻案风”,写“小评论”。这时正值老兵退役前夕,连队几乎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魏成和几个老兵合写了一篇《八连为何入党难?》的小评论,登在墙报上,并吵吵闹闹要搞什么“火线入党”。那天半夜里,我被隔壁的吵嚷声惊醒了,只听一个确定退役的老兵说:“……你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身体不行啦,耗子尾巴生疖子------没多大脓水了,早晚也会有今天,何必这么……”“啪”的一声,像是指导员的工作手册摔到桌上。他声音从来没有这样激动:“不错,我早晚也要走。不过到我转业时给你捎封信,让你知道共产党员是咋个走法。我就是转业,也只是从部队转到地方,而决不是从党员转到群众……”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时,那个老兵已经走了。只见指导员一手夹着卷得粗大的喇叭烟,一手顶着胃部来回踱步。我给他换了一杯茶,一屁股坐要椅子上,赌气地说:“哼,现在是浑身扎刺儿的人吃香,照这个弄法,我还不想入党呢!
”
“嗯?!
”指导员唰地扔掉喇叭烟,在我对面坐下。抚摸着下巴上涨得通红的伤疤,气喘喘地盯了我足有半分钟,又猛地拉开抽屉,稀里哗啦翻出两张纸,“这是你的申请书,拿回去好好看看!
搞清楚了再来找我吧!
”
那一夜,我捧着入党申请书,又久久没能入睡……
这年年底,我调到司令部当保密员,就跟耿志分开了。听说前不久,他因日益严重的胃病又住了院。出院以后,就确定他这批转业了。按团领导的意见,让他休养一个时期再走,但他执意马上到地方报到,并坚持说他行李不多,搭退伍老兵的车顺路,不要再单独给他派车了。就这样,他、耿大嫂和五岁的女儿小真真就乘上了我们这台车。
真想不到呵,昌隔两年,他果然遇上了“今天”!
我的老指导员呵,我佩服你的过去,你给了我多少智慧和力量呵!
可今天,你脱下了军装,没有了军职,还能给我什么帮助呢……想到这里,我的心又紧缩了。一车老兵,一天的路程,这艰难的旅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仿佛是在一条失去了帆和舵的船上,被起伏的波峰一会儿高高托起,一会儿又重重摔下……
天渐渐亮了。云,被欲来的大雪压得低低的。风卷起砂粒打得车篷噼啪作响。团首长带着部队来送行了。我在车尾碰到了刚同大家告别后走来的耿志。多日不见,他似乎又苍老了许多,脸上黑色的皮肤把颧骨裹得更紧了。他手扶车厢板,扭过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巧呵,我接你出来……你送我回去。”我本想说说请他多帮助的话,但不知怎么搞的,一瞥见他那失去了光彩的帽子和衣领,却怎么也张不开口了。虽然常说:当兵是一喜,复员更是一喜;当兵是入校,复员是毕业,可谁也不认为复员比参军光荣。面对这位解了甲的老上级,我怎好再给他提出一大堆难题呢?耿志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朝我微微一笑。
欢送的锣鼓敲响了。喇叭里开始播放欢送曲。在一片激动的告别声中。车缓缓地驶向营门……人总是这样,当一件珍贵的东西整天放在你身边的时候,并不怎么觉得它的价值,但当你一旦失去了它,却会感到它是那么珍贵,那么不可缺少。此刻,一道营门,好象成了军和民的分水岭。老兵们这会儿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已踏上民的边界了。他们------包括刚才还怪声怪气地哼着“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的魏成在内------几乎全都探起身来,久久地、无言地朝着渐渐远去的首长、战友和一排排整齐的营房招手。呵!
车上第一次这样的安静……
我知道,他们留恋着这火一样的生活,对鲜艳的领章帽徽,怀着深深的感情……耿志呢?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虽然和耿大嫂坐在车尾,但他没有起来,反而低着头,搂着小真真介睡熟了一样。紧闭着双眼。只是在车身颠簸,他稍微仰脸的瞬间,我看见他下垂的睫毛上闪亮了一下,……半响,又听到小真真嚷道:“爸爸,你把我搂疼啦……”
上了山间公路,车速渐渐快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下雪了。风卷着雪片,呼啸着穿过车篷。耿大嫂连忙垂下车后的篷布,车厢里开始有点暖和气了,但空气也沉闷起来。经过一早上的折腾,老兵们疲倦了,在拉着头昏昏欲睡。连小真真都缩在耿志的怀里,慢慢阖上了眼睛。我心里默算着:二百五十公里,保持三十迈车速,也得八、九个小时,现在,才刚刚开始……
“真真、真真,别睡觉呵,当心感冒了!
”耿志轻声唤着小女儿,同时使劲瞅了我一眼。哎呀,怎么忘了临行前军医交待的话了?寒冷的清晨在车上打瞌睡容易感冒。耿志是在提醒我呀。我急忙装着很随便的样子,捅捅身边的杜小满:
“老杜,回去打算干点啥?”小满 也是八连的兵,入伍入党都比我早。他人很利落,尽管退伍了,仍很注意军容风纪,好象明天早上还要出早操似的。
他揉揉眼睛,笑着说“庄户人家嘛,回去不种地干啥?”
小满的声音不高,但却像一条线,牵动了老兵们的心。车厢里顿时活跃了起来。大家从工作扯到家庭,又从家庭扯到父母、对象和带回家的见面礼。小满从一个大个子兵的提包里抽出一本书,举起来嚷嚷:“大个子还没到家,就钻研土壤学啦,等他搞出点名堂,说不定还能上报纸哪!
”憨厚的大个子被逗得满脸通红,大家开心地笑了,眼睛里第一次露出“毕业”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可惜这良好的气氛让魏成煞了风景。一个瘦瘦的老兵问他:“回去干不干饭馆?”
“还干饭馆?”魏成唰地拉开大提包的拉链,抓出几块饼干,“那这几年兵不是白当啦?”
魏成家在县城,母亲是县里一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国。据说魏成在下乡的两年里,表现还不错,后来他妈想办法把他调了回来,安到了饭馆里。魏成不愿意干,经常和他的一帮“朋友”到处蹓,征兵时,他妈又想办法让他参了军。我早就知道他当兵的目的之一是借退伍的机会调换个工作,但没料到他会这样坦率地道出他的秘密。
魏成喷着饼干末末,含混不清地说“往后有啥事尽管来找,咱是非党人士,没那么多原则,好说话!
”说着,拿眼去瞟耿志。
耿志依旧揽着真真,像是在嗅着孩子的发香。
“怎么,他到底没入党吗?”我低声问杜小满。
小满轻轻一笑,把嘴靠近我的耳朵,悄悄讲了魏成的近况。
魏成原打算在最后一年使把劲,到年底解决组织问题。在耿指导员的帮助下,年初也确实好过一阵。但终因“动机不纯”吧,总免不了干一阵看一阵,犯些冷热病。其实对魏成个人来说,入不入党也没啥关系,将来照样拿钱吃饭。无奈家庭方面压力太大,据他母亲来信讲,不入党到了工厂很难进科室,还得当“小工人”。他实在交待不过去,只好写信让母亲帮忙。他母亲曾多次给耿志写信,名义上是了解儿子的表现,实际上暗示能否照顾?对这些信,耿志一封一封都做了答复,耐心解释魏成没有入党的原因。到了今年年初,上级确定耿志转业。连以下干部原则上哪来哪去,耿志自然要回原籍。魏成得知后,马上写信告诉家里,他母亲紧接着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对耿志的身体表示关切,并提出耿志在县城的工作不用他操心,县里的关系她很熟,完全可以帮忙,尔后又谈到了魏成的入党问题……第二天晚上,魏成满怀喜悦地找到了耿志,他们谈的什么没人听见,只是小满在接夜里第三班岗的时候,连部的灯还亮着,隐约听见指导员说:“魏成呵,这样入党不是害了你么……”
……
小真真一直偷偷看着魏成蠕动的嘴。她咽了口唾沫,咬着小手指头,悄悄凑到妈妈耳边问:“妈妈,夫夫(叔叔)吃的什么呀?”
耿大嫂抬手在她头顶上轻拍了一下:“小馋虫……”边说边向自己身后摸索。
魏成高兴了,他用手择时夹着两片饼干,逗引地说:“叫党员叔叔,叫了给你,嘻嘻。”
耿志一把揽过真真。“对叔叔说,俺不要。”耿大嫂边说边摸索得更急了。
真真望着那两片饼干,摇摇头:“俺不要,俺有带玻意(璃)纸的……”
魏成得意起来:“脱了军装了,现在都是老乡,干嘛见外呢?叫党员叔叔,快。”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正待说话,老兵们冒火了,七嘴八舌地数落魏成:
“算了吧,钻腾了五年,到这里过起党员瘾啦!
”
“哼,没脸没皮,丢我们的人!
”
“有本事到地方干出个样看看,当兵几年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怪胎。”
杜小满一把抓过饼干,塞到了孩子手里。耿大嫂涨红了脸。耿志仍旧一言不发。魏成却满不在乎地打了个哈哈……
……
“不好!
”耿志喊了一声,猛地掀开了篷布,就在这一瞬间,我才五个小时以来第一次看到他脸上往日的光彩。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一跃而下。等我和小满几个人跳下车的时候,司机和助手正蹲在后轮边,一脸苦相。耿志忙问:“怎么回事?”
司机瞅了一眼他的没有帽徽领章的着装,没有答理他,而是朝我一本正经地作了报告。耿志的脸色又黯然了,嘴角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情况好糟。汽车右轮陷进了半米多深的大泥坑里,泥浆和着冰碴碴,使车轮打滑上不去。显然,需要人来推。我向老兵们说明了情况,动员大家下来推车,同时也好减轻车的负荷。耿大嫂抱着小真真也下来了。但我喊了几遍,还是有几个老兵不愿下车,有的还埋怨开了:
“怎么搞的,睁着个大眼往泥坑里开!
”
“唉,这身新衣服算是交待了,谁让我推,谁给我洗。”
“大冷的天,让模范作用好的下去推吧,咱没那个觉悟!
”这又是魏成。
杜小满和几个老兵望着我,皱起了眉头。我也呆住了。这车单靠我们几个人是推不动的。怎么办?!
我真想骂他们几句。突然,一只大手又按住了我的胳膊,紧接着是耿志平静的声音:“来,咱们先试试,你到前面去,叫司机发动车吧。”说着,就听“通”的一声,耿志已经脱去棉鞋,挽着棉裤跳进了泥坑,用肩膀紧紧顶住了陷得最深的右后轮。泛着冰碴的泥水淹没了他的膝盖……
我浑身一阵发热,迅速扒下棉鞋,跟着跳了下去。杜小满等几个老兵也相继下了泥坑……见此情景,车上的老兵们不吭声了,他们默默地下了车,很快站到了推车的位置上。魏成最后一个跳下来,但很不情愿地转到车左侧,找了个干燥地方,
引擎猛地吼了起来,连拉带推,终于轰然一声,汽车冲出了泥坑。
听着引擎欢快的叫声,司机笑了,我也笑了,大家都笑了!
我回头一看,耿志却被轮子溅得满身泥水,寒风一吹,冷得他直打战战。他脸色苍白,右手使劲顶住胃部。耿大嫂抱着真真走过来,真真搂住耿大嫂的脖子“妈,爸爸冷……”耿大嫂想说什么,但在耿志严厉目光的逼视下又咽了回去。这时,司机奔过来,双手恭敬地递给耿志一条雪白的毛巾……
大家分散开来,坐着休息。这一折腾,不似刚才那样冷了,只是肚子有些饿。我又想到了真真,便向大个子要了半包饼干,拿着去找她。正巧,她妈领着她从耿志那边过来了。
我扬起手里的饼干:“真真!
”
真真叭嗒叭嗒地跑过来,险些滑倒,我连忙扶住她。
“饼干,玻意(璃)纸的饼干!
”真真的小手高举着一个彩色塑料袋,里面是玩具饼干。
“哦,你也有哇!
”
“夫夫(叔叔),爸爸让我给那么多夫夫(叔叔)吃!
”她说的那么真挚,那么急切,还踮起小脚,把饼干直往我怀里塞。
耿大嫂跟着走过来,把手里捧着的三包饼干递给我:“拿着吧,大伙匀着填填。”原来预计路上有兵站吃饭,所以大伙带的干粮不多,有的干脆没带。这路上一折腾,大伙肯定饿了,但也不能要耿大嫂的呀。我说什么也不要,直到大嫂要生气了,才勉强收下。
大伙吃着,说着,有几个老兵甚至有心思爬上了就近的小山坡,眺望起雪后的山川和原野。我舒心地坐下了,拿出一片真真给的饼干,放进嘴里细细品尝着……此时,我觉得身后有一只大手撑着我的身子骨,硬朗朗的,并不单薄……
该上路了。我去叫耿指导员上车。找了一圈,没见着他。我又往前走了几步,一阵风吹来,听得小山坡的灌木丛后传来说话声,先是魏成的声音:
“……再说那么多也没用了。算我向你作最后一次请求吧,要求不高,只希望你给我们单位头头介绍一下我的情况,说明我在部队是发展对象就行了。余下的事好说,反正你已经分到我妈厂里,她是一把手,办成了,房子任你要,工种任你挑……”
沉默……
我止住了脚步。天哪,耿志竟分到了魏成妈妈厂里!
“不行!
”这是耿志斩钉截铁的声音。
魏成强词夺理地:“现在的青年不都是发展对象吗?怎么就该着我不是呢?”
“发展对象是经过党支部研究,列入发展计划的同志,你还不够格。”
“那好,咱们走着瞧吧!
”魏成愤愤地说。
沉默……
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车赶到县城的时候,已是午后五点多了。按说,这里是我的终点站,在这,我要把老兵们一个不少地移交给县武装部,然后再由他们负责送往各个公社。至此,我们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就要解散了。
老兵们拥下车来。贪婪地打量着家乡的“都城”。他们大概在想:家乡呵,我回来了!
可我想的却是:任务呵,接近尾声了!
我整整军装,迈着轻松的步子跑进武装部的大院。一切都很顺利,武装部的首长接过档案,甚至还赞赏地打量了我一眼。我长吁了一口气,快步走出来。一仰脸,呵!
太阳从浓浓云层的罅隙中露出脸来,把余辉洒向大地,雪后的山川被抹上了一层金粉,像我的心情一样舒畅,欢快……
耿志一家子在离人群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大人都没说话,只有小真真还有点重返故乡的味道。我望着正在沉思的耿志,猛然意识到,我就要和他分手了。凝视着这位老上级,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得阵阵作痛,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惜别之情?我说不上来。就在我打算走过去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我们路上误了开饭时间,又急着赶路,沿途兵站给武装部打了电话,让他们准备一顿饭。这时候,两个同志正把一饭筐热包子抬到院子当中。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又饿又乏的老兵们就一拥而上,团团围住了饭筐。我一看这情意,肺都气炸了,急忙赶过去,大声喊道:
“大家排好队,别挤!
”我的嗓子都变了音。
但是喊声被这一片闹嚷嚷的声音淹没了。也许是到了终点站算是彻底退伍了?尽管有杜小满和几个老兵在阻止,但一些人仍嘻嘻哈哈地争着,挤着,有的甚至抓了五、六个,狼吞虎咽地吃着。武装部门口过路的群众停住脚,好奇地看着这一堆半军半民的人们。怎么办?能让这次行军结束在这顿该死的饭上么?能让老兵们的最后一站停留在这乱哄哄的吵嚷声中么?我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忽然,魏成高声嚷了起来。原来他不知为何来晚了,没拿到包子,正叉腰站在空筐旁,拉着个架子骂骂咧咧地要和谁吵架。我没辙了,脑袋嗡嗡作响。恰在这个时候,我身后突然“啪”“啪”!
两声响中,紧接着传来了小孩的哭声。我一回头,呵,是小真真!
只见她紧抱着一个热腾腾的包子,张开小嘴,猛扑在妈妈怀里哭起来。耿志脸色铁青,下巴上的伤痕涨得通红。他追过去,指着真真手里的包子,生气地说:“你怎么好拿叔叔的包子呢?叔叔还要赶路……”
“不!
是夫夫(叔叔)给的嘛……”小真真哭得更伤心了。
耿大嫂连连拍着真真的后心,望着耿志,心疼地说:“孩子冻了一天,也没吃口热饭,你竟这样狠心打她……”这个贤惠的大嫂眼圈一红,哽咽了。
老兵们------包括魏成,都静静地站着,十几双眼睛从不同的角度一齐注视着这里。
耿大嫂抽泣着说:“……风里雪里,你走到哪儿,俺娘俩跟到哪儿,没说过一句扯腿的话……你心里有啥不舒坦,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呀……”她说不下去了。
耿志打孩子的手微微颤抖了:“你扯到哪里去了,你不懂部队的事儿,这里的饭菜是照老兵人数备下的,咱们是搭车……再说,他们吃了还有山路要赶,咱家近,忍忍就过去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急忙赶过去,一把拉过耿志:“指导员,你也太认真了,大伙再能吃,也短不了孩子的……”我正要回头去哄真真,却见真真慢慢地走到了魏成跟前,用她那冷得通红的小手举起了包子,抽抽嗒嗒地说:“党言(员)夫夫(叔叔),你饿,你吃吧!
”
魏成愣住了!
慢慢地,他脸由青变红,又由红变青,眼皮低低地垂着……半晌,他机械地推开真真的小手,含混不清地说:“我……我,叔叔不饿。”
“不,我刚才听到了,你说饿。”说着踮起脚尖,硬把包子塞给了魏成。魏成呆呆地拿着包子,头垂得更低了……
……真静呵,大家都看着自己手里的包子,谁也没有抬头。那几个抓了五、六个包子的老兵,悄悄地走向了饭筐……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把真真轻轻交给了耿大嫂。该移交了,我想下达“集合点名”的口令,可转念一想,还走这个形式干嘛?前面已经有了好几次教训了。但一抬头,我愣了------在耿志的左侧,迎着风一字儿排着我的十六名老兵,连魏成在内,一个不少。大家庄严肃穆的挺立着,那神情决不像已经解甲归田,倒像是一列正待命出征的勇士!
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庄重、威武的阵容,这队伍时每个人的身上都好像喷出一股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我被这气氛感染着,激动着。不由得整了整前襟和军帽,高喊一声:“立正!
”以标准的队列动作跑步到耿志面前,向这位没有领章帽徽的指导员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礼:
“报告指导员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参谋,傅军光。”
耿志以军人特有的敏捷,有力地抬起右臂,就在大臂块与肩平的瞬间,他并拢的五指微微颤抖着停顿了一下,眼角滚下了两朵晶莹的泪花,但随即就以更加坚定的动作,敬了他的最后一个军礼……
夕阳的余辉衬着他那瘦削而坚挺的身架,像一幅剪影,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他那举起的右手,好像永远、永远也不会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