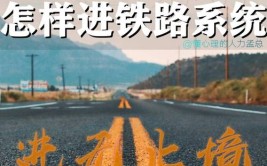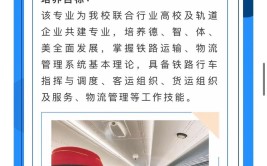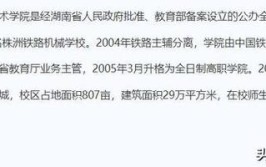召唤我奔赴战场
远去了,一次次回头张望
我们浸渍在岩石上的

血液、汗水
像朵朵绚烂的鲜花
定格在如血的残阳
——摘自旧作《告别成渝路》
墓地前的追忆
襄渝铁路北碚车站背后山坡上,有一片茂密松林,林间有铁道兵烈士墓地。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我拨开没胫的荒草,一眼看见了铁道兵六师政委朱耀洲的坟茔。斜阳里,我的身影投向他矗立的墓碑上,像是向他敬最后一个军礼。四周寂静无声。秋风里隐约传来他亲切的话语:还记得当年成渝铁路上那些往事吗?记得!
怎能不记得!
那段经历,是我人生难得的一次奇遇。
那是1950年的11月上旬的一天。筑路大军一夜奉命撤离,去了朝鲜战场。出我意料,全团只留下我一人。在仓促而紧张的气氛中,老领导临别用手指了指前方,你去三十里之外的黄家大院,找朱耀洲政委领受新任务。
天明,我沿着一片狼藉的工地前行。
怎么偏偏留下我一个人呢,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一回多过瘾!
我在二野军大学的正是作战。可这话只能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口。时近中午,橘林深处,露出黄家大院一角,我顺着蜿蜓山道往上爬去。远远看见一位身披军大衣首长模样的人,站在大院门外石梯上眺望。见我爬上来,忙喊通信员跑下来接我。通信员指着你的背影对我说,他是朱政委。我们大队人马也刚从歌乐山赶到这里,政委刚才还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流窜,正准备派人去接你呢。
你像兄长那样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你说大部队都走了,剩下的路谁来修?眼下重庆失业工人众多,刘邓首长决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接替部队修路。为此,军区组建了我们这支队伍,授予“西南军区工程委员会筑路第一支队”的特殊番号。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早日修好成渝路。
今天的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当年重庆刚解放面临的诸多困难。兵工厂停工了,黄包车没人坐了,银行歇业了,学校因生源不足无法行课。重庆市劳动救济委员会动员失业工人、黄包车夫、职员、失学学生……参加修路,分别组成产业工人队、黄包车夫队、职员、教师学生队……还有“游民队”。他们是从全市收容来的流浪人员。
三百多游民,编做三大队第五中队。你在干部会上严肃宣布,不准谁喊他们是“游民队”。派淮海战役战斗英雄陈牛儿担任中队长,陈牛儿没文化,你要我多去他那里。
我在五中队发现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个叫李荣贵的河南人,年近五十,在台湾修过多年铁路,会开山放炮的绝活,因为想家,回到内地,流落重庆街头。当时我们缺的正是开山放炮的手艺人。我向你报告了他。你立刻让陈牛儿通知李荣贵带上工具,到各队示范,工效猛增。你提名李荣贵当劳动模范。有人背后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你严厉批评他们农民意识,鼠目寸光。
冬天逼近,失业工人衣衫单薄,你派我回军去当面向首长报告。首长当场拍板,把国民党被服厂存放的棉衣,统统发给他们。我去李家沱被服厂办交接手续,厂里问我要不要棉帽,我擅自做主:不要!
为什么?工人们穿上国民党军装又戴上帽子,岂不成了一群俘虏!
要不得!
棉衣发到工地,你看见许多工人故意把棉衣反起穿,把白布里朝外,你哈哈大笑,你们好样的,不当“俘虏兵”!
这次回军区,我悄悄打听,上朝鲜的那些战友咋样了?回答是:他们大多牺牲了!
我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对你讲了,你神情黯然,沉默良久……
夕阳西沉,我告别墓地。对那段筑路日子的回忆,也就由此绵延……
邓政委叫我们去修路
为了不惊扰睡梦中的重庆市民,天还没麻麻亮,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西南军区驻地浮图关。直到东方破晓,我才从欲散的雾霭中,看清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浩荡声势。走在最前头的是警卫连,连长扛“开路先锋”的大旗,晨风中猎猎招展。我跟着通信连紧随其后。回头望去,逶迤的队伍,在山中忽隐忽现。
昨天(1950年6月15日)上午,我正在南温泉军大操场上操练正步走分解式,突然喊我出列,回营房打背包,赶往几十里之外的西南军区大操场,限定两点前赶到。
我走进军区大门,远远看见操场上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除了军人还有宰蓝制服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幸好有人跑过来,拉着我躬下腰往人群前面走,我顺从地跟着,走到前排,那人把我往地上一摁,顺势坐下。猛然拾头,主席台前横标上写着:成渝铁路开工典礼。我如梦初醒,汗流浃背地赶到这里,原来是参加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啊!
主席台上坐满了首长。我只见过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他们来学校做过报告。其余的都不认识。大会由李达参谋长主持。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讲话,讲成渝铁路的历史由来和现实重大意义。刘伯承身材高大,第二个轮到邓政委讲话了,不知谁眼疾手快,身轻如燕地冲到讲话席前,忙把麦克风急速从高处降落,邓政委从容走来,恰到好处。
邓政委即兴讲话,讲得很随意。他说成渝铁路不能不修!
谁来修?派部队!
当前部队征粮剿匪,任务重呵!
我和伯承、贺龙同志商量,把我们身边的警卫团、通信团抽出来,再从军大抽出一批学员,充实到战斗部队里,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筑路第一纵队”,这个番号我军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它标志着我们军队,能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到工地好好地向铁路工程人员学习,莫说二话哟。什么是说二话?我这个来自下江的学生不懂。别人告诉我就是不要发牢骚。呵!
我记住了这句风趣的四川方言。
晚上军区后勤杀猪款待我们。正吃得高兴,团长找我,拎给我小红绸包着的一包东西,孙参谋(见习),这个由你保管。一看我便明白,是我们直属二团的印章:四四方方的是大公章,用于公文;长条钤记,写便笺用;还有团首长的签名印戳,用于人事任免。团长说你不忙跟团里大队人马走,先随通信连去架电话线,好熟悉一下地形,顺便画个沿线地形图回来。
架完线的那天黎明,我一身军服全被露水打湿,只好躺在长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让江风把衣服吹干。忽听有人喊我,团长派马接你来了。牵马的是个陕北老兵,刘志丹的部下。这样老实巴交的老同志来牵马接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说没啥,没啥,革命分工嘛,井冈山的骡子资格再老还不照样驮炮。我没文化,让我喂马,知足了。
当兵的不会修铁路,忙拜那些“穿蓝马褂”的铁路员工为师,他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亲热地喊我们“穿黄马褂”的。不几天,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活小事,困扰着咱当兵的人。时值盛夏,一种叫墨蚊的飞虫肆虐,别看它肉眼难见,特别欺生,专咬外来人。咬得大家浑身都是疙瘩,奇痒难熬。害得有人不敢上茅坑解手,那里是墨蚊的大本营,弄得有人叫苦不迭,屁股遭不住啊!
后勤处忙着发万金油,头几天管点用,几天下来,墨蚊喜欢上了这种凉咝咝的味道了。它吸人血的同时也享受这清凉滋味,驱之不去。这些转战南北的老兵,在墨蚊面前,无可奈何!
正当大家无可奈何之际,一位小卫生员竟把它征服了。小卫生员西安人,文化不高,鬼机灵,他偶然发现遍坡浸野长着青蒿,无意间扯了一把,用手搓揉,鼻子一嗅,气味难闻。正当他扔掉它的一瞬,突发奇想,它或许是墨蚊的克星!
忙把青蒿汁液涂在大腿和屁股上,专门去蹲茅坑,守坑待墨蚊,蹲了好一阵,墨蚊逃之夭夭,不敢来犯!
他边系裤子边喊,墨蚊被我收拾住了!
团里马上把这发现报告给纵队,纵队首长立即通报所属各师、团推广,小卫生员立了三等功。
当时伙食标准很低,营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天一毛四分钱,只能顿顿吃南瓜。老兵发牢骚:井冈山吃南瓜,陕北吃南瓜,如今修铁路还南瓜,打个饱嗝都是老南瓜的酸臭味。话传到了邓政委耳朵里,他拍板,每人每天增加一毛八分钱。邓政委说部队修铁路,劳动是创造了价值的嘛。从此,每天能打一顿饱牙祭。大家笑豁了。
伙食尾子有了结余,团政委不同意分钱,要给每个干部战士买件有意义的纪念品。这件事交给我办。这点钱能够给全团近两千号人买个什么呢?我估算来估算去,够每人买支大号金星笔。政委说好,就买金星笔!
管理员背着一大把钞票,跟我去重庆解放碑最大的一家文具商店,这是笔不小的买卖,经理笑脸相迎。派人去全市各个文具店调拨金笔。
经理夸我们好眼力,全市只有他们有上海的钢笔刻字机。凡是在这里买钢笔,免费刻字。只需把要刻的字写在纸上,工作人员像变魔术似的,手握机器把柄,跟随所写的笔迹转动,机器另一端的针尖,便依样画葫芦在笔杆上刻画起来,毫不走样。经理讨好说:它是馈赠亲朋好友和情侣的上等礼品啊!
我及时纠正他的话,我们是发给部队每个人的。我自行作主,每支笔刻上“军工修筑成渝铁路纪念”。抹上金粉,闪闪发光。发到干部战士手中,个个如获至宝。都把它装在丝线编织的钢笔套里,别在上装口袋。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的时尚。可惜我这支笔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失落了。
作家孙谦来成渝路体验生活,写电影剧本。纵队首长让他到我们团来。我们这里有崇山峻岭。政委让我陪同他。在陡峭的山崖上,战士们腰系麻绳,挥舞铁锤打炮眼,做鹞子翻身的惊险动作,孙谦老革命连连大呼精彩!
临走,孙谦向我透露,剧本拟名《成渝铁路》,他还向我讲了某些生动的节。后来他的剧本在《电影文学》上发表,写一位筑路工程师,爱妻子也爱吹笛子,牺牲了,孤零的一支竹笛,在水井里飘浮。其实蛮感人的。可惜在批判《武训传》的鹤戾声中,它也难以幸免,剧本天折。大家便无缘看到那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成渝铁路》了。
不拿枪的战斗
这里是不拿枪的战斗。
我们支队担任重庆至永川间的路基工程。猫儿峡隧道早在解放前开凿完成,涵洞则由川东行署负责完成。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按铺轨的先后,准时交出踏基,铺轨先从大渡口铺往九龙坡,再到菜园坝,我们每天扳手指算进度。
民工的劳动所得,每日赈济两公斤大米,约折合成人民币二角八分钱。我说个当时币值的参照系:我因公外出,事务长发给我午餐补助一毛五分钱。可以到饭馆炒小份蒜台肉丝八分钱;血旺豆腐汤五分钱,外搭两分钱的米饭。所以,他们这点收入,仅够糊口。
然而,他们的劳动热情极高。每当傍晚收工号一响,自发的“支援抗美援朝”,行动开始了!
挑着泥土,抬着石头,飞快奔跑,喊声震天:“多挑一挑土,捐献飞机大炮!
”前后持续一刻钟左右。这道壮观的风景线,在几百里的工地上绵延起伏,让百姓赞叹不已。
为赶工期,必须开夜班。没有电灯,何以照明?在人力密集的平地,摆几盏电石灯,坡上则用竹竿悬挂汽灯。电石灯往外嗤嗤喷吐火焰,气味很不好闻;汽灯烧煤油,要打汽,灯罩是石棉丝织成的,很娇气,一磕碰,就瞎了。得派专人维护。搬石运土的人,手持熊熊燃烧的纤藤杆,在黑暗中穿梭,又是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
当时的爆破技术非常原始。尤其是炸药,用芒硝和木炭混合制作,全靠土法碾细拌和。危险性极高!
尽管领导再三叮嘱把细。加工、运送炸药,要远离火星;装炮时,只能用特制的尖细的竹筒,往炮眼里轻轻倒药……然而,悲剧还是时有发生。
一位来自重庆银行系统的中队长宋中桥,在一次加工药时,不幸烧伤了脸颊。幸好发生地离重庆不远,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疤痕。他出院时,朱政委要我送他回家休息几天,并向家人表示歉意。我见到他的太太,人很漂亮,通情达理。老赵执意要随我回工地,他说快铺轨了,我能安心呆在家里吗?他太太默默地送了我们很远,我很感动。记住了这个倔犟人的名字。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永川工地,被炸药烧伤的是个姓张的青年学生,长相英俊,又肯吃苦,首批吸收他入团。朱政委问他,将来路修通了最想干什么?他不犹豫地说上大学。朱政委得知他烧伤,亲自打电话给队长:组织最精壮的人力,轮换抬滑竿,火速送到永川。终因伤势过重,在半路上牺牲!
我们心里很难过,在工地上为他开了追悼会。
我们天天盯着作战形势图看,猜想到我们迟早要上战场。军区首长让我们抓紧办一件事:从一万失业工人和七万民工中,挑选出一万人来,组建西南筑路委员会下属的工程总队,移交给管理部门。我们闻风,分头赴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各行署所属各筑路指挥部,一一落实。此举就是大家说的“民工转正”。一时间,像参军那样热烈,选中了的,兴高采烈;没选上的,垂头丧气。日后他们成了铁路上的中坚力量。至今有人戏称,它是成渝铁路的“黄埔一期”。
钢轨是这样炼成的
一天,朱政委喊我去他那里,交给我个出乎意料的任务。军区政治部约我写篇修筑成渝铁路的长篇通讯。在此须补上一笔,朱政委入伍前,在山西老家是小学教员,文笔很好。在成渝工地上,给军报写稿。每每在稿件上添上我的名字,我沾他的光,报社真以为是我写的了。他把盖有政治部大印的介绍信交我,要我抽时间外出采访。我笑着对他说,我这个“南郭先生”要现丑相了,他说我手下没有“南郭先生”。
成渝铁路的钢轨,是怎样炼成的?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
为解谜团,我先去两路口重庆管理分局(成都铁路局前身)所在地。分局设在闹市的街边,要不是一块白底黑字的长吊牌挂在木柱上,我还以为这里是商店。在简陋的办公室里,见到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陈琯。他身穿米色风衣,戴副大墨镜,学者风度,和蔼可亲,全无官场上那套俗气。他要我去大渡口第29兵工厂(稍后改为101厂,今天的重钢),去找一位铁路上派到那里的检验员,一位上海姑娘。我按约定时间去了那里,她知名度倒还蛮高,不费什么力就找到她了。只见她头带大檐帽,身穿蓝制服,有几分“铁老大”的傲慢。接过介绍信,把我这个大兵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把盖有军区政治部大关防的介绍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可能是苏联反间谍故事片看多了,怪异的表情,有点令人啼笑皆非。还好,她终于说,算你找对人了!
在去车间的路上,她津津乐道她的检验工作,什么荷载强度,摩擦力,韧性……名词术语信手拈来。我心里想,铁路上派她来,派对了!
路上我看见坝子里荒草没胫,有的机器还躺在草丛中睡觉。百废待举的感叹,油然而生。这里是用从水路上运来的鞍钢钢锭,轧成钢轨。没有钢花飞溅,金蛇狂舞的壮丽景色。它倒像个产房,期待一个新生婴儿的出世。机器的轰鸣声似乎正为新的生命欢呼。出模的钢轨,开始有些犹豫,欲行又止,几度停留。我替它捏了把汗!
但是,它不肯退却,积蓄力量,作最后冲刺!
终于如婴儿呱呱坠地,人们一片唤呼。
上海姑娘告诉我说,在这之前,试轧的历程,艰辛而曲折。这台带动轧钢的蒸汽机,是一百年前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花银子从英国买回来的,搁置武汉。抗战期间,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把它从战火中抢运到这里,它通身凝结着爱国者的心血。如今垂垂老矣,返老还童,实属人世间奇迹!
第一根钢轨的诞生,是民族精魂的见证!
后来上海姑娘告诉我,轧轨纪录,日日刷新,最高时一天轧出136根38公斤标准轨。
大渡口钢厂,不愧是一个时代的骄傲!
铺轨了!
先从大渡口铺到九龙坡港口码头,迎接从水上运来的第一台火车头。部队把二营营长张济舟,调往铁路上当铺轨大队长。老张找朱政委“说聊斋”,不想去。政委说你去最合适。当年你在淮海战场上,凭一把军号,吹得敌人心惊胆颤,成了战斗英雄。拿出当年的猛劲,肯定能把铺轨队带成尖刀营。
我去老张的铺轨队采访,他让我开洋荤头一次坐轨道车,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旧藤椅,让我坐在轨道车平板上,我说要得个球!
他一笑,你是上级机关来的,理当照顾好你。我拉他一起坐在尚有余温的钢轨上,聊起铺轨队的事情。老张说铺轨队真辛苦,和打仗差不多,工人很累,我能办的就是下班了给他们整点烧酒喝。老张果然把铺轨队带得响当当的,远近闻名。
当时发动沿线百姓捐献枕木,在朱杨溪铺轨时,我恰好碰见一位留着胡子的乡绅,把自己上好的楠木寿材贡献出来。几根乌黑发亮的楠木系上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工地,煞是闹热。
几年前我编《通途》时,收到重庆工务段蓝光武副段长的散文,写到当年乡亲们捐献的枕木,有几根还没有退役,这些珍贵木材做的枕木,比沥青浸制的枕木都结实。当时我突发奇想,办一个成渝铁路历史陈列馆,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永远存放在馆中,留给后人看,一定非常有意义。
钢轨铺设好了,可火车头又怎么弄到重庆来?贺龙司令员请求军委派登陆艇,把它从武汉运送到九龙坡码头。我沾张济舟大队长的光,把我送到九龙坡港口,看火车头从码头底下用绞车一步步绞上来。那天码头上人山人海,难怪呵,没有出过川的山城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火车头这个庞然怪物!
激战驷马桥
我随部队从重庆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一年半有余,终于到达成都。回首望去,漫长的成渝路上,留下了我深深浅浅的脚印。
师司令部驻扎在成都东升街一处独院,据说解放前是某个绅士的小公馆;政治部则设在庆云南街,和四川广播电台一墙之隔。去那里办事,要穿行好几条闹市。
我们一到成都,就遇上绵绵阴雨,罗师长的脸上有些阴沉,他让我去成都气象台问问,“五一”节后天气是否有持续晴天?我带回的是坏消息!
他用手来回在发青的络腮胡上摩挲一阵之后,坚定地说,孙参谋,从明天起,你跟我去驷马桥工地。
一听驷马桥这个地名,不由得想起写《长门赋》的司马相如。当年他去长安,卓文君含情相送,在成都郊外一座木桥桥头泣别。他对天发誓:“相如不驷马衣锦,绝不汝下”。然后策马西去。汉武帝派他出使西南夷,官居“副部级”。
回成都时,果然驷马风光,万人空巷。从此“驷马桥”和一个爱情故事,便流传下来。我不敢对罗师长说这个故事,怕他说我小资情调。
驷马桥大填方,是通向成都火车站的咽喉要地。成为成渝全线“七一”通车的拦路虎!
川西行署集结数千民工,日夜奋战,指挥这场战斗任务的,正是身经百战的罗崇福师长。
天上时时下雨,地上处处泥泞。罗师长幽默地说,孙猴子的金箍棒把天戳破了,害得我们大家遭淋。他披件雨衣,到处察看,发现问题,把队长(军队派遣的干部)喊来,如此这般,当面吩咐。风里来,雨里去,从黎明到黄昏,我日日跟随在他身边,从没见他高声训斥过谁。民工很喜欢这位不拿架子的首长。他不时从雨衣里摸出相机,拍下感人的劳动场面。一群年轻的打夯女工,唱着号子,有节奏地抬起夯墩,重重落下。号子是她们即兴的脱口秀,看见罗师长来了,一点也不怯生,长声吆喝唱道;罗师长呀,嗨呦,会照相呀,嗨哟,给我们呀,来一张,嗨哟。罗师长忙不迭举起相机,大声对她们说自——然——点——,咔嚓一下,一个个泥猴笑逐颜开。
民工用鸳篼挑一挑泥巴,从陡峭的跳板往上攀登,如过奈何桥。一挑泥巴,一路上被雨水淋,被鸳篼沾,最后倒在填方处,已损耗许多。罗师长为此发愁,摸着络腮胡沉吟良久,一拍大腿,对我说,快把后勤处长叫到工地来!
当时成都市民吃的大米,是私人作坊用谷子碾成,师长吩咐后勤处长到作坊收购碾米的下脚料——糠壳,把它撒在跳板上,撒在鸳篼里。果然效果很好,跳板上的人脚下再不滑溜,鸳篼里也不沾泥巴了。许多加工米的作坊老板,本来碾一点卖一点,听说驷马桥工地急需大量糠壳,连忙开机打米.一时间,部队运糠壳的汽车络绎不绝,百姓端茶送水相迎。
驷马桥填方所需泥土,从附近的荒地提取。一天下午,放晴。忽然有人气喘吁吁跑来,向罗师长报告,一民工挖土时,被无人荒冢的死人骨头戳破了小腿,血流不止。师长命令我:你去,用我的小吉普,把受伤民工送平安桥铁路医院,越快越好!
我从铁路医院返回,罗师长给我讲了一件难忘的往事。那时,他是刘邓二野战军的旅长。在攻洛阳古城的战斗中挖战壕时,一名战士被死人骨头戳伤了腿,团长向他报告了,他没当回事,攻城在即,这点伤不算什么,抹点碘酒就行了。不料这个战士因破伤风死亡!
邓政委知道后,严厉批评他:身为旅长,不懂起码的医学常识,不懂得爱惜战士的生命!
他至今都很自责。
激战四十多个昼夜,驷马桥烂泥疙瘩变通途。当张胡子率领铺轨大队,雄赳赳气昂昂,把最后一锤,落在最一根钢轨的时,顿时,轨道旁的旷野里,鞭炮齐鸣。大家兴高采烈地站拢来,紧挨着罗师长合影留念。
罗师长忽然满面春风地喊我,跟他去成都最豪华的耀华餐厅吃红烧鱼。我以为我们辛苦多日,犒劳下自己,理所当然!
罗师长说今天是为你送行。接上级电话,你马上回重庆大军区另有任务。什么任务?罗师长神秘一笑:不知道!
我猜他知道,不肯说罢了。正是这个电话,决定了我未来的命运——奔赴朝鲜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竟在东海岸的诺东江边,与罗师长不期而遇,战火的缝隙里,我们说起驷马桥难忘的日日夜夜……
第一趟客车
我乘坐的是成渝铁路的第一趟客车,但不是通车典礼的彩车,是试运营列车。卖票,站站停,为的是让列车员来次热身演习。
上车后,意外碰见从工地上来的王勤珍。她原是我们那里的巡诊医生,找领导磨嘴皮,硬要来当列车员。只见她开始忙碌起来,先在每个茶几上放两只茶杯,外形有点像白瓷笔筒,只是没有那么高。红色路徽很醒目也很喜庆,下有“重庆列车段”字样。是江西景德镇烧制的。
散完茶杯,开始冲茶,要不要茶叶?免费供应。
坐过火车的农民,回去逢人就说,火车上真安逸!
好看的女娃子给我们掺茶,下车还喊慢点走,我敢打包票,解放前的地主都没享受过这福。
茶刚冲完,她又捧起个木匣子,满车厢问:哪位看小人书,任你挑选!
工人旅客抢着要看;农民则不太热心。她便想着法子哄旅客高兴,给他们唱歌,说快板。小王嗓子尖,很甜。我笑着对她说,过去你在工地当医生,红汞碘洒,抹了就走。还真没发现你是个歌唱家的天才。她抿嘴一笑,所以来当列车员!
等列车上有了广播,当广播员,让我的歌声响遍全列车。
车上的乘客,大多是沿线农民。男的穿着粗布长衫,手持烟杆(车厢里不能抽);女的头裹白帕,或手牵小孩。他们不是走人户,也不是赶场,是专门来感受火车的滋味。他们当中,或许有把上等寿材献出来做枕木的长老,或许有箱子里压着清朝“银票”(成渝铁路股份)的人,或许还有血气方刚之士,当年为了保路,投奔资中杀了端方,星夜驰援成都……
小王报站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只见她垫起双脚,在车门的上方卷动什么。仔细一看,她手里的白布卷,突然跃出几个红字:——“前方站:柏林”。此柏林,非彼柏林,乃是永川附近的一个小站。当时,车上没有广播,列车员只好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向旅客预报站名。为了不让一个人下错车,她们又想出招数,把重庆至成都的各站站名,印在长长的细纹白布上,用木棍做轴,卷成圆筒。每开出一站,用手卷动一次,把前方到站及早展示旅客眼前。倘若这个白布卷被人收藏至今,一定又是件珍稀文物。
前方是栏杆滩车站了。我猛然想起,修筑铁路时被炸药严重烧伤的小张,就埋在这山沟里的竹林深处,下葬那天,我说把他的头往铁路方向靠拢些,好让他能听见汽笛声。小张,汽笛唱响了,听见了吗?我把头伸出窗外,月色下竹影朦胧,汽笛在山坳里久久不散。
午夜,车停内江,小王该换班了,她邀我去宿营车休息。她一边走一边对我说,星期六我们段同重庆车站联合办舞会,你能来不?我轻轻摇头;那再下个星期六呢?我依然摇头。她似乎有些失望,怎么不能来呢?只好撒谎说,说我要出趟远差。其实此行是去朝鲜战场。
黎明时分,车抵成都,站台上有辆军用吉普车等着我,把我直送剑门关,追赶出川的大部队。突然,王勤珍跑到我身后,塞给我半包没吃完的江津米花糖,拿着,路上吃!
想不到在我奔赴战场的前夜,意外地和一位在铁路工地上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重走了一回成渝铁路,我很感激她。听说她后来调往了贵阳,假如她还健在,希望她读到这篇文章。当然,还有那位忘了名字的上海姑娘,还有远去大西北的肖光瀚……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剪彩者为贺龙元帅
(编者注: 成渝铁路,简称成渝线,是中国境内一条连接四川省与重庆市的国铁一级客货共线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成渝铁路全长505千米,1950年6月,成渝铁路全线开工;1952年6月竣工,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
作者简介
孙贻荪,笔名江南雨,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江海海陵(今泰州)书香世家出身,幼读经史。长江帆影,运河桨声,时时入梦。童年在抗日烽火中担任抗敌儿童团团长,穿越封锁线,送鸡毛信;青年时代作为战地,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用文字抒写战火中的壮丽青春。
因诗罹祸,如无根之萍,在筑路工地上漂泊二十余载。重新握笔,写散文和散文诗。散文集《风雨人生路》《回望岁月》《别样人生》获中国作协、中国铁路文联联合举办的中国铁路文学奖;散文诗集《独坐黄昏》获首届天府文学奖。
曾担任自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川南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成都铁路局文联常务理事;中国铁路文学奖第三、四、五、六届评委。
来源:《自贡文联60年文集 散文篇》(原标题为心中的那条路——纪念成渝铁路开通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