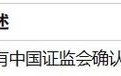二、三沙阴天亦光影
当天下午,离开杨家溪仙气飘飘的古榕树林,司机把17个观光客送到三沙光影栈道。
我们从三沙海湾高坡西侧的栈道入口开始漫步下行。这里能看清“光影栈道”全貌:木条栈道一层一层和缓地竖直降维,方向朝东南、朝海边蜿蜒,在临海的山崖上拉出一条自西向东、先下后上的优美曲线。栈道落到谷底后,紧贴曲折的海岸迂回前行,抵近一片亲水的金色礁石、礁盘,突然开始朝东偏北方向逐渐抬升,缓慢地离开海岸,最后是一程长长的、包含着上上下下的东向登山运动,终点是设在远处海湾大桥旁的景区出口。

阳光从厚薄不匀的云层中漫射出来,背阳方向的海湾泛着浅绿、有时含蓝的颜色,一排排浪花相互协调,共进共退,反复拍打曲折的岸线,似游嬉,似纠缠;逆西斜的阳光朝右望去,海面灰暗,偶尔也染点金色——以我为界,左右两边大海的色彩截然不同,这表明视网膜上接收到的朝阳或背阳的光影波长不同,它由人眼的朝向决定。这也是关于人(或别的观察者)观察与否、站在什么角度观察、如何观察,就会能动地影响微观物质(如光子)“行为”的神奇现象?
三沙光影栈道-朝左(东北方向)观望时的东海光影
三沙光影栈道-朝右(西南方向)观望时的东海光影
世界真奇妙。
大家一路观赏,偶尔也停下来拍照,脚下的高度在逐渐降低。
我靠近了海边,踏上海水冲积成的石滩,躲闪着乱石间的坑洼、孔洞、明缝、暗隙,小心翼翼地在或圆、或斜、或尖棱的乱石上以足尖“碎步”,最终站到一块朝海里倾斜的淡黄色大礁盘上,海拔立即归零。
礁盘上那细细的麻面,是海水千百年孜孜不倦地啃咬的痕迹,还是由地壳开裂时流出的含气岩浆凝成?石面与鞋底的摩擦力很大,居然一点不滑。我慢慢前行,走到不断扑打、挑逗“游客止步”牌的海浪跟前,扶住深褐色的仿原生态木桩而故意扭曲的水泥栏杆,直面东海大舞台的最前沿,凭海临风,观看海浪与海岸韵律、节奏分明的聚散。这是大海平静时的心率图,海里波涛列队成阵,间距分明,秩序井然,轮番冲来,黄色的礁盘、礁石或前挺或后伏,将涌上来的波涛撞碎成无数浪花,然后消失。这种循环往复的音像,像一部雄壮的乐章,一场盛大的歌舞。海水如此强大的节律性运动,步调一致,前赴后继,昼夜不停,是谁在指挥?
此时-脚下海拔归零-我已贴近海面
这是警示“游客止步”的仿原生态木柱般扭曲的水泥栏杆
被层层叠叠的浓云遮蔽的太阳,用力将面前的朦胧拨开,偶尔现出金色的轮廓,在海面上映出一道由远及近的光晕;然而,形态各异的黑灰、蓝灰、白灰色的阴云继续朝太阳涌动,捍卫着“阴间多云”的天气预报。只有当云层遮蔽太阳的活动稍息的时候,海空漫射的阳光立刻渲染,金辉闪耀。这时,长条形的,放射状的,鱼鳞斑的云含红、含黄、含蓝,甚至连最阴暗的乌云也妥协成灰色,三沙的光影便凄美、诡异、壮丽起来。
我很想延长在海边的时间,为了拖住大家的脚步,我斩钉截铁地反复“预言”:随着夕阳继续西斜,空中的金色会向绯红变幻,出现赤橙黄绿的多彩光影。实际上那只是摄影家们坚持、却不一定变现的关于阴、晴各有高下的信仰。遗憾的是,我的“预言”被现实打个粉碎,海空后来的演变越来越差强人意,刚才拍的几张金光熠熠的照片,已是三沙滨海在这个下午最美的一抹亮色。
这是从“北大荒”开始风雨同舟-共同走过半个多世纪之路的三对夫妇
当天下午三沙光影栈道上空最美的一抹亮色
由于一步三回头地观察、拍照,我已落到最后。
开始追赶。上坡的步道和无数名山的山路一样上上下下地捉弄人,那是栈道的故意,是在协助山海光影留人的美意。然而,这番美意却令“70后”老童们有点尴尬:发福的老龚难以消受上上下下的待遇,撑着拐杖还时常要停步坐下喘气;年龄最大、中风后腿有微疾的老傅拖住原连队卫生员渐渐落到后头;少年时受过足球训练的更生站在台阶上测心率,是心动过速卷土重来(据说运动履历多会留下心脏故障)?他见群里唯一的房颤病人赶了上来,便顺手给我搭脉,说也超120,应当歇息。一路追赶,我本未觉异常,经他提醒,立即有了心脏蹦出胸腔的感觉。4年前在衢州攀登江郎山,为了抢先登顶,我和阿亮还能在爬山路上奔跑对决,如今我已英雄气短。令人诧异的倒是拄着登山杖、迈着八字步,在栈道上踉跄的成华,居然一直走在大家的最前头。
三沙光影栈道-暮云下的东海、小岛和海湾群山
三沙光影栈道-我们的最后一瞥
一群70后老童的囧态,都被三沙海湾笑着记在心里。
三、霞浦最俏是滩涂
霞浦海湾多,浅处是滩涂。潮涨时滩涂与外海连成一片汪洋,潮落时水尽处现出泥滩,水浅处漂浮着网箱,还有规模宏大的海藻晾晒场。无论泥滩、网箱、晒场,都是海边人顽强谋生的迹象,是海边生活日常与自然景观的融合。在地理位置、朝向与潮水性情特殊的海湾,这种融合便造化出奇景秘境。
出游的第二天上午,旅行车开进沙江镇,拐进一条狭小巷弄,在一个T字路口停下。这里高矮不一的民房交错,像内陆小城不起眼的一个角落。这与号称“沙江S湾摄影基地”有何关联?下车后大家跟司机踏上一条更窄的坡道,坡上的房屋更加密集,左侧立着一座天主教堂。过了教堂,司机转进一幢灰色水泥楼的跨巷门洞,在一个小窗前买票。窗边一张白纸,几个大字歪歪扭扭:“门票每位15元”。
我实在难以将这副场景与“一不小心惊艳了世界”的景观联系。
霞浦-沙江村S海湾
霞浦-沙江村S海湾-岛上还有渔村
上了楼梯,灯光开始明亮,有了点公共场所的眉目。二楼是灰色毛坯,通栏无窗、一个粗糙的内平台,设了几排固定的长凳。我们站了上去,一片海湾跃入眼帘,立即让我暗惊:密集的竹竿一排排竖直插在水中,呈S形曲线阵形,朝远处延展,漫漶在整个海湾。这是养殖、晾晒海带、紫菜的广阔“水田”,它细节精致、纤巧、优美,线条悠扬、静谧,场景宏阔,气质非凡。这是我未见识过的新奇,确有“一不小心惊艳了世界”的震撼。
听说观景还可更上一层楼,大家忙跳下长凳,一涌而上。
顶层是楼顶平台,毛坯依然,却是全视野。
为了让世界看到霞浦,有关机构曾在这里拍摄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宣传片《大美霞浦》,“沙江村S海湾”就是其中主角之一。平台比楼下高几米,视野与滩涂的俯视角也稍增大。我不懂,这片2016年就打动世界的景观,观景楼为什么至今仍然这样潦草马虎?
9:15,老天依然阴沉,头顶是乌云,到远处逐渐淡化为或深或浅的灰色,下沉到朦胧的远山发白。偶尔,阳光钻出云缝,斜射几道探照灯似的“丁达尔光束”装饰海湾。海天交汇处,群山连绵,水墨画似的海面,林立的竹竿使我想起印度洋边的斯里兰卡科格勒海滩的海钓。海钓作为落后的生产方式早被印度洋遗弃,浅海滩里插着的一片木杆林,每根木杆上坐一个肤色漆黑的渔民,是专为旅游业在作“海钓秀”,舞动着海钓杆下不知真假的小鱼。海钓的场面小,远没有沙江海藻场的恢弘阵势,更无轻歌曼舞式的齐整、舒展。尤其是晾晒场中间那条拉运海带、紫菜的S形水道,三两条小船在游弋,是海湾的点睛之笔。
沙江村S海湾的右侧
沙江村S海湾-晴朗的傍晚美景(官网照片)
阴天的沙江湾上午,似诗,似画,竟还有几分渔歌唱晚的意境。
午后,我们离开具有300多年历史的霞浦溪南镇畲族古村落“半月里”,驱车前往牙城镇南湾村,观看海上迷宫,滩涂“甲骨文”。
据说,因村民与景区争议尚存,“甲骨文”景区的防腐木栈道铺设了一半被村民截停,无法连接公路边。为了阻拦拐进半截土路的汽车,村民还修筑了工事——土包和坑洼,致使人行亦艰难。司机告知,当天潮水要两小时后才能溢满滩涂,“甲骨文”显现佳境。是原地等待还是至观景台“点到为止”,让我们自由选择。于是, 17人一分为二:9人在烈日下越过村民布下的封锁线,踏上平整的栈道,到达居高临下的观景台;另8人在车上休息。
旅游途中但凡遇事,我大多立场积极,所以也站到了观景台上。
“还等什么潮水,这不就是‘甲骨文’吗?”我惊呼。
霞浦-南湾村滩涂-未经海潮删减的“甲骨文”
霞浦-南湾村滩涂的“甲骨文”-照片上部左右两条水道是正在进入滩涂的潮水
南湾甲骨文,本就是因养殖和村民赶海的需要,在滩涂上垒起的长长短短、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围堰和具各种曲率的矮堤。有人偶然发现,涨潮时海水涌进滩涂,部分围堰、矮堤被水淹没,水面上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笔画”,很像甲骨文字。这种并非刻意的笔道,后经人为测算与设计,改造围堰、矮坝,使水淹滩涂时“甲骨文”弄假成“真”,以假乱真。
这时,潮汛被月球引力牵拉,开始朝滩涂缓慢涌动,远方的海水像无数涓涓细流,顺着枝杈般密集的沟渠缓缓朝周围扩张,极慢、极慢。两个小时,原来是指滩涂开始涨水到满潮所需的时间。
眼下,广大、干涸的滩涂满是白色盐渍,就像铺展开来、厚薄不匀的宣纸,无意堆垒或有意构筑的黑色围堰、矮坝,都是“墨写”的“甲骨文字”,不过未经水面删除、修饰,“原稿”的“字”多、间距小、挤在一起,影响了审美。观景台老板递来手机,里头存有最佳“甲骨文”照片,画面上“文字”被海水删得只剩寥寥数字,每字只有寥寥几笔,有的像游鱼,有的像弯臂,还有的像没有完成的“八”字或“人”字,依靠绯红的云霞映照,蓝色的海水衬托,围堰的金色闪烁,果然有比现在更美的光影。
霞浦-南湾村滩涂-这是我们没有等到的“甲骨文”修改篇(网络照片)
(同上)
大家没有静等两小时的耐心,只能与滩涂甲骨文的“修改稿”擦肩而过。
读一次“原稿”也不错,何况“两稿”如同天气阴晴圆缺,氛围、趣味、境界等都不相同,各有自身的长处嘛。跋涉了一段热气蒸腾的田间,才艰难地站到观景台上的9位英雄这样安慰自己,也相互安慰,然后仍心存不甘地别了南湾滩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