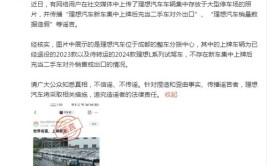前序
修建窄口水库,我已记不清去过了多少趟。刚开始去窄口,我估计是1969年的暑假还是秋忙假,现在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我会去了水库工地?真的说不清。
记得当年,水库工地的一切还都未开始,大坝的坝基处还是一片乱石滩,清澈的涧河水由南向北哗啦啦地流着。空中的天,蓝蓝的;太阳高照着,特别的美。涧河水不是很大,经常看见人们在水中的石头上洗衣服。衣服洗完,晾在无水有草沙滩上,收工时也就干了。当时人们去干活,好像大多是挖沙备料。水库西边山底下的泄洪主洞貌似已经开工,当时我也不曾去看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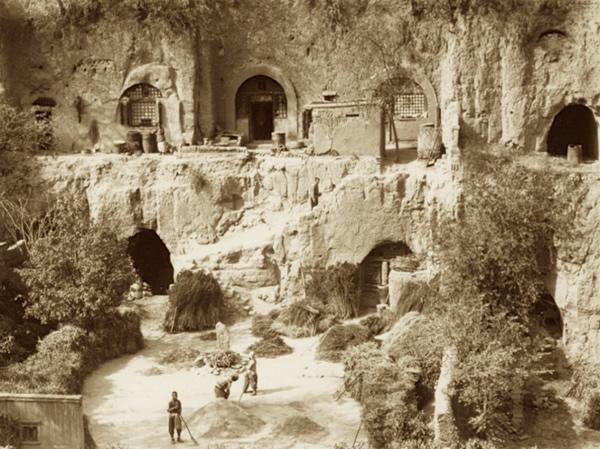
当年人们去了以后,在大坝坝基往南,库区1公里的东面山坡上有一个村子,村民已经迁移,原住房还未拆除,所有修水库的民工全住在这个村子里。记得我们村子当时的一行人马有好几十人,全部住在一户人家的木板楼上,人挨着人,住得满当当的,晚上打呼噜的声音那是震天的响!
记得当时库区有一个唯一的公厕,片石块石泥巴垒起的围墙,1.4--1.5米的高度。每每想起一句歇后语,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想起这里的茅厕何偿不是如此!
后来所干的工作是拿上钢丝刷子,清理坝基东面的山坡底部,每块石头都刷得很仔细,目的是让混凝土沙石与山坡能够很好结合。
清理东山根,是先要在这里修一个导流洞,把整个涧河的水先导入到该导流洞中流过,来保证大坝能在无水流的状态下正常开始施工。
导流洞不是很大,1.5米左右的宽度,大概2米来高。用成型的水泥仝块锢成。待洞子修成,涧河水引入时,平时看似其貌不扬的水流,进洞时十分湍急,人不小心掉进去,会立马把你冲到几百米开外的出口去。干活的过程中,倒是见过有人不小心,把装石头的的藤条大筐从入口掉了进去,嗖的一闪,就不见了踪影。
这样一来,修建水库大坝就一直可以处在无流水的状态下进行,待主泄洪洞打通,再把水流从泄洪洞排过去,从而再封死导流洞,来保证大坝施工的正常进行。最后是什么时候封死的导流洞,如何封死的,我没有经历和目睹过,从而不得而知。基于这样一个施工工艺,对后面所讲的大坝合龙,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两边开始堆料,到中间时的最后一车土即是合龙吧。
后来大概是1970年3-4月的时间,人们去上工,来往穿梭于导流洞上,擦肩而过。肩上扛的劳动工具如:羊镐、铁铣、抬石木杠、藤条大筐、三爪石头夹等,时不时的会挂破别人的衣服。
工地干活主要是清理坝基,炸药炸,羊镐刨,铁铣起,人工抱,大筐装,杠子抬等等。也没有人叫过苦、喊过累,也从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这时库区搬迁的民房已经拆除,人们已经转移住到了库区外面下游田地边上有土崖的窑洞里了。具体情况,印象不深,已经记不清楚了。
一、筑坝
后面再去的时候大约是1970年10月左右,大坝上土,修筑大坝。净一色的架子车拉土,排着队往大坝上倾倒,待东方红拖拉机推土机推过后,就是拖拉机拉着个大钢锟的碌碌来回碾压。这是一个直径大约1.5米的圆筒形钢锟碌碌,它的表面全身长满了圆台形锥剌,其高约0.2米,保证经反复碾压后大坝土质的密实度。
这个时间,我们村一行人的工种主要是,保证大坝东山边角,在机器压不到的地方的土质密实,用人工抬石夯猛砸。石夯是一块0.4米见方,0.6米高的六面形石块,用两根长木杠靠铁丝绑夹起来的工具。七、八个人分别抬在木杠的两头,在劳动号子喊声的作用下,一起抬起,一起落下。石夯抬起的高度在1.2米以上。只听见一人喊到“同志们哟”,大家齐声答喊“哎哟”,随着喊声,脚下的步伐向前一步抬起石夯,后退一步石夯落下。“把夯抬起来哟”,“哎哟”;“修水利哟”,“哎哟”;“为人民哟”,“哎哟”。随着号子的喊唱,石夯一窝一窝往前砸。
大坝土质密实度是否达标的检查是由施工技术员进行把关。技术员们拿一个直径和高度大约分别为10厘米的定型圆筒形钢圈,在压打过的土坝上精心取样,通过称重,再拿着计算尺左右拉一下,游标左右拨一下,从而计算出压砸过的地方土质的密实度是否达标。不达标继续压砸,达标后方可进行后面一层的上土施工。
计算尺可以做乘、除、函数、对数等运算。当时一把计算尺要将近20元左右,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因为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中专毕业生起始月工资才28元,更不用说水利民工每天几分钱的工日值了!
这样的计算尺工地上当时比较多,可以随处见到。后来上了高中,才知道了计算尺的使用方法。当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准备的白光硬纸简易计算尺好像是1元一把。知道了使用方法,还曾有过打夯时要是能随地拣一把该有多好的想法!
当时打夯过程中,上了年纪一点的村民也和一些水利工程队上年纪较大一点的可能是工程技术人员攀谈,内容无非是收入之类。当得知每月能发200多元工资时,立马让在场的我们都惊掉了下巴,真是让人羡慕,工资真是高呀,农民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1971--1972年期间为读高中时间,还算在学校专门呆了两年,未曾去过窄口, 1971年的大会战场面我也不曾在场。
1973年初春时节,读完高中的我又一次来到了窄囗水库。这次大坝主坝已建到规定的高度,主要要干的是大坝北面坡的垒石加厚。不同形状的块石要从几百米之外用架子车转运过来。拉石头的车子要通过一路慢上坡才能把块石运到施工现场。由于劳动强度太大,虽说本人当年已过18岁,怎奈身材瘦小,个头太低,连队強烈要求让我回家。尽管当年在家里我是担水挑粪拉车样样拿手,所以我不服气,想留下来。结果,以大队为单位的水库连队领导为我配备一位比我还瘦弱,年龄又小的男孩作为搭档装车拉石上料。
和这位小搭档一起拉运石头,路上他后面推我前面拉,艰难往前还勉强可行。当把石料拉到施工现场时,我傻眼了。只见路的这边全是石块,路的那边是施工现场。现场十分像电影中的炮楼,上面和下面全是干活的人群。路的这边和炮楼上面,两处之间有十余米的深处,石头还没有砌上来。连接两边的是两块20厘米宽、6--7米长的两块木板。要把一车石头送到对面施工处,必须让架子车的两个轱辘压着两块木板类似于过桥一样,飞一般的穿过才行。木板桥的下面全是施工的人,假若架子车在木板上走偏翻车,后果可想而知!
看着这场景,不服输的我,腿肚子直打哆嗦。还好,这时邻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原中学同校学长接过我的车把,两只脚在木板上左踩右跨,嗖的一下,让一车石头从木板上穿了过去。这就是那个年代,真悬啊!
我要真心感谢这位邻村的同校老学长,不是他我还真不知道怎样把这一车石头送过去!
直到现在,将近50年了,记忆仍然犹新,场面使我终生难忘!
鉴于此,第二天,我还是卷起了铺盖卷老老实实地回家了。假若造成了安全事故,我还真的担待不起这个责任。
二、清碴
时至1973年后半年、1974年和1975年,又好几次去了窄口水库。这两年去窄口,仍然住在田地崖边的窑洞里。窑洞里没有床,地面上用石头围起来,垫上炉碴,铺上麦草,再把自带的褥子铺上去即可。卫生状况可想而知,身上生虱子是不可避免的。
这段时间主要的任务是清理开挖发电厂的厂房基础,以及大坝北面废石和泥渣。这里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人力架子车拉运。如若碰到大型石头人难以搬动的,先放原处,最后集中放炮炸碎再运。放炮炸石也很简单,在石头适当部位用黄泥围起一个窝,装入硝酸铵炸药,插上装了引线的***,再用黄泥封严即可。随后记住装炮的数量,各类人员躲避到安全区域。专人点燃引线后,也躲到安全区。听炮响数量和装炮数相符时,说明完全爆炸了,皆大欢喜。若不符,说明有哑炮,就必须把哑炮排除后,才能解除安全警戒。排除哑炮是十分危险的,假若哑炮是延时时间过长了,是真的延时爆炸,对排除哑炮人员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也许是1974年春天吧,在清台转碴的过程中,现场上石碴堆积得像小山一样,起码有近百米高。地面上的人用架子车往外转运石碴,我们的任务是在距地面数十米的高处石渣半坡清理出一个平台。刚开始,连里的人一字排开,用洋镐刨,铁铣连挖带扔。待场面能够转开,开始用架子车转运。起初,架子车的转运距离也只有不足5米。有那么一次,我推着车子,到边缘时,没掌控好倒碴的时机,结果车子冲出边缘,整个架子车顺着立陡的碴坡冲了下去。眼看车子冲过一段距离后翻掉了,车架和轱辘分离,车架顺着渣坡自然慢速下滑一段后停止。车轱辘翻滾着撞到了坡底的边墙,已经扭曲变形不能使用了。没有了架子车,今天的工也上不成了,也就没有了工分。这样,只得把车架从碴坡上拽下来拉放到一边空地上,我和我的搭档推着变形扭曲的车轱辘回住地找人修车。待车修好后重新再去上工。
记得是1975年的春季,任务是从大坝北面坡底转运石碴到长桥街北出口处倾倒。一人一车,自装自卸。刚开始拉碴,车架上放有围挡竹圈。竹圈是一个长大约5米,宽0.4米左右的竹编物件,专门用于架子车上装运土类石碴等各类散装物。由于竹圈太费,用不了几次,竹圈即被挂破,就不能使用了。后来干脆改用木板箱围挡。木板箱长约1.4米,宽和高分别约为0.6米和0.4米。这样装满一车石碴大约0.3方左右。
记工是按照每次拉运的方量和次数计算的。还好,从装运现场到石碴倾倒场是一路慢下坡,虽然运送距离有一两公里,但一人拉一车石碴倒也不觉得有多累。晚上零点上班到早上8点,记得跑了20多趟。
歇工返回连队住地,为了能减少负重,往往把车架留在工地,只把车轱辘推回住地。单推车轱辘还是一件比较有技术的活种。因为车杠钢轴较低,要么绑好两个木棍推行,要么让车轱辘处于半直立状态,单手推行。绑木棍推行比较麻烦,一般没有人这样干。车轴半直立状态是指,让单边轱辘着地,让杠轴和地面有一个80多度的夹角,在高处一边轱辘由一只右手抓扶,掌握好平衡,推上边轱辘,下边轱辘外沿将在路面摩擦旋转前行。若方向掌控不好,车轱辘很容易跑偏。下次上工时,再如此把车轱辘推到工地,放到车架下,便可继续上工。这种方法,比较方便,往往都用这种办法单独推回车轱辘。当年去过窄口水库工地的人,很多都会这种推车轱辘的方法。真是实践出真知!
这一次修建窄口水库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库区清碴会战劳动模范。不过未能参加颁奖大会,到后来回家后的8、9月份好像,生产队长给我带来了奖状。本想和奖状一起应该还有一个带有“窄口会战劳动模范”字样的洋瓷缸子类的纪念品呢,结果让我失望了。队长说沒有!
最后奖状也未精心保管,早就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因为,农民要那东西没有用!
在整个窄口水库的修建过程中,除了东方红拖拉机,其余工程机械均未看到过。有拖拉机是因为洛阳有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再有就是用柴油机带动卷扬钢丝绳自制的爬坡器,用于在陡坡处拖拉上坡送料的架子车。好像只是在水轮机、发电机的安装现场看到过起重机在吊装。挖掘机、大型汽车运输机械等一概没有。就连偏心配重电动打夯机这个小玩意儿,只是听传说,现场也不曾使用。
不过在清碴休息的时间里,倒是见过一台很先进的设备—盾构机。当时不知道叫盾构,我们把其称为掘进机。它被放在大坝东北方向、长桥村的东南方向的山脚下,这里可能是灌流引渠的第一隧道口吧。当时好像试掘进时,已经清理出了一个圆形的工作面。我和同伴也在该机器周围转了一圈。其长度大约有10多米,掘进刀头的直径大约有2米多。在圆盘形刀头的径向方向上,分别垂直布置着多个锥面圆滾刀具,可能是靠刀头旋转时用锥面圆滾刀具实现对岩石的切割碎石而掘进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重的设备,当时也不用蓬布覆盖保护,放在那里任凭日晒风吹雨淋,就像报废的设备一样。在随后的日子里,一直未听说过该设备投入使用。这是我一生最早见过的实物盾构,也是唯一的一次。
前面讲了连队民工的住处状况。吃饭食堂也是在崖边一孔窑洞前用油毛毡搭建起的临时建筑里生火做饭。主食大部分时间是手工糊糊面、玉谷面馍、白水煮萝卜、咸菜,有时只有辣椒水。偶尔遇个节什么的还能有个油条或者喝个羊汤什么的。不过也是凭票供应,拿票打饭。这比在家里的生活状况还算好点。
有那么一次,闲暇之余和同伴一起,去了一位本村同姓老哥处,他在给省水利工程队工作人员做饭。该工程队在大坝北面约500米的西山根公路旁边。工程队的院子用木板等栅栏围挡,房子也是净一色的油毛毡盖顶的临时建筑,不过这里不住窑洞。去时正赶上这位老哥揭着馒头锅。只见揭出锅的和未揭出锅的蒸馍箅子上都有10个左右雪白的圆形馒头,顶部还镶嵌一颗红枣,馋的我们口水直流。不过老哥也不曾相让,我们也不能硬讨,必定是人家的定量!
只是呆了一会,讨了口水喝后,便离开了。
记得时间进入了1975年6月,一天下午我们休班,正在窑洞前洗衣服。忽然听见所在住处往东方向稍偏比一点两三百米的地方人们在喊,好像是出事了。这个地方应该是灌渠通过的地方,他们在半山腰炸石,要清理出一个台基。炸山的飞石,往往都会飞到我们连队住处的窑洞前。听见喊声,我们几个同伴前往。看到现场把我们惊呆了,只见一串血迹脑浆沿着刚清理下来的利石石块长坡,顺撒了长长一串,足有10多米长。血迹的终点处,一个人正躺在路边,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现场太惨烈了!
后来根据位置描述,我猜想这应该就是所说的程村水利战士罗米发。之所以是猜想,是因为我当时一来不认识罗米发,二来压根不知道这里是哪个兵团哪个连队的工地。
后来过了不几天,我的此行任务完成,时间到期,便回家开始收割麦子了。
三、开洞
时间到了1976年3月左右,我和同伴又一次来到窄口水利工程工地。这一次驻扎在宋曲附近,准备为窄口灌渠宋曲长隧洞开挖做准备。
刚到驻地时,窑洞有限,必须自己动手先解决住宿窑洞问题。当然,干这类活对我们显然不在话下,和同伴两人一起,在连队附近一个高地崖边上,两天时间内就把窑洞打好了。这次住宿条件还稍有改善,用木棍、废木板等分别绑扎了两个小床,不用打地铺了!
不过刚打出来的窑洞太湿,为了防潮,把包装尿素肥料用的大塑料袋剪开,钉在窑壁的墙上。过了一段时间,明显发现塑料纸袋靠窑壁的那一面渗出了好多水珠珠。
窑洞的门也是用木棍、废木板、树枝、玉谷杆等绑扎起来,挡在洞口上,用铁丝拧个扣,可以和立栽的木杠子锁起来以利安全。
干活工地在距连队住地大约有1公里多,这里的半山腰上的一个沟壑处。这里是灌渠隧洞的北端出口。我和同伴先在这里清理了洞口表面,随后开始了放炮开挖。
放炮当然是先在岩石硬土上打眼。打炮眼时,一人手扶钢钎,一人把八磅大锤抡圆了击打钢钎的端头。最长1.4米左右,直径3公分的钢钎,当然也有短的,其刀头部位是扁锥形,边打边转,最后形成一个一米多深的圆形炮眼。有时大锤砸在扶钢钎同伴的手上是常有的事。
由于隧洞断面较高,所以分为高低两个工作台面。记得当时一上工,我和同伴就被安排在高处的工作台面上。我们也十分乐意在这个区域干活,因为这个区域靠近洞底工作面,安全系数是最高的。这个台面也是洞顶的半圆形工作台面,前后面深大约1.5米到2米左右,左右洞宽大约5米左右,高也就不足2米。每次我们打完眼放完炮,由下一个班组来清理碴石,用架子车运往洞外。
同样,当炮眼打到1米左右深时,就可以装炮了。这时可以把一定量的硝酸铵炸药小心翼翼的送到炮眼的底部,并把插好引线的***埋设在炮眼中的炸药里压实,再用红土等封好前部炮眼。这时记清装炮数量,点炮后,人员全部撤到洞外安全的地方。同样,当响炮数量同装炮数量相符时,表明非常顺利,观察排险后,方可下班,只待后一班组来清理碴石。否则,仍要清理哑炮,为清理碴石的班组清除障碍。
这样如此,一直干了好些天。当隧洞深度大约有30米左右时,洞的正顶方有一块石头,像早晨升起的太阳一样,正一点一点的向外露头。因为我等在平台之上,距离这块石头最近。我亲自见证了它开始露头,到半米、一米、两米、直至几天后,随着洞深的增加,它全部暴露了出来。它的长度大约有5、6米,宽大约2、3米左右。看起来是石头,但在洞顶基本也沒有凸出来,和四周也没有松动的迹象。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记得是六月还是七月的一天,这块石头的后端部分已经距离高处台面洞底工作面大约三米多时,刚好处在下层工作面的正上方。那天晚上12点我们上班,和往常一样,打眼放炮排险后,没有发现异常,8点钟我们下班休息,下一个班组上班清碴。
时间到了大约10点钟,正在窑洞里睡觉的我,听见外面有人说,洞子里出事了,塌方了。后来证实就是那块石头掉下来了。它的平面大约有一间房子天花板那么大。并且说,北营村的张勤学受伤了,好几个人轮流抬着送去了五亩医院。
后来听连队干部讲,张勤学是在让大家撤出时,他在最后,被落下的那块巨石挤在洞壁上,伤到了内脏,在送往五亩医院的途中,一路喊痛的他,当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随后,全连所有人员心里十分难受,情绪低到了极点。为了保证隧洞的开挖进度,兵团又调来了别的连队接替了我们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就转移到了洞外。
四、背石
来到了洞外,我们的工作就是备料,为洞囗筑渠准备石料。由于找石头在靠连队的右边这条沟里,要把石头从这边沟底背到沟顶,再顺着沟顶小路把石头扛在肩上背送到洞口。连队住地、捡石头沟底、洞囗基本上类似于一个等边三角形。
为了减少背石头时对衣服的磨损和石头对肩膀的损伤,往往带一个护肩的肩牌,就叫护肩。石头沟崖高要百八十米。往往是从沟底背上石头爬上崖顶,下来再背第二块,也送到崖顶。为了保证背送石头的过程中有休息的时间,就这样让两块石头交替前行。
当把石头背送到洞口时,还要把它垒起来,以便能够量出方量,才能根据方量为你记工分。背的石头形状有块石,有片石,也有较大的鹅卵石。反正是能背动的石头都在备料之列。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好像也是在背石头。我们住在窑洞里,避震也是不能忘的。记得自己在枕头头顶的窑洞壁上打进去一个铁钉,用线绳吊了一个瓶子在枕头边上,还想着晚上睡着时若瓶摇摆,碰到头上,自己就可以醒来,立马跑到窑外。
这样一直到了1976年的9月9日,下午4点,我刚从捡料沟出来,准备下工。往前几十米,出了前面的沟口就到连队住地了。这时,崖上边团部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周恩来?一月份已经去世了,现在公告?什么意思?我正在纳闷,过了几十秒钟,喇叭中又重新传出声音“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才知道毛主席去世了。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水利工地各个角落人们无不如此。兵团等也在宋曲设立了灵堂,人们排队前去悼念。灵堂里庄严肃穆,哀乐响起,时不时的能够听到人们的哭泣声。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到了10月10日,早晨一觉醒来,走出窑洞,到处贴满了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各种标语,铺天盖地。全国上下又进入到了批判四人帮的洪流之中。
时间又过了不多久,我们的时日到期,又打起了行装回家了。此后也就再未去过水利工地了。
附记
在窄口水库工地期间,有时也要干一些与水库无关的活种。时间好像是1975年的某一天,连队住地还在长桥村东的田地崖边。连队安排我和同伴去项城煤窑为连队拉煤,并到灵宝买些咸菜。本来往返40多公里的路程,一天应该是很轻松就回来的,怎奈那次外出还是让我记忆深刻。
上午吃过早饭,我和同伴拉着平时拉石碴的架子车出发了,大约4小时后到了灵宝城里。很快,买上了咸菜,下午时分返回到了项城煤场。拉煤的人真多,队排得很长,大部分都是各连队来拉煤的。煤场上真干净,丁点煤也没有。直到大约下午6点多,我们还没装上煤。从煤窑出来一车煤,立马就被下边等待的人给抢光了。
不知到了几点钟,我们终于装好了一车煤,月亮已经老高了,这时才拉着煤车往连队赶。一路上饥渴难耐,人困马乏。走了好长时间,终于走到盘龙村了,又饿又累,同伴建议,找点吃的垫一下。随后我俩敲开了路边一家院子的门,一位大妈听说了来意,立马为我俩拿出了两个馍馍为我们垫了肚子。谢过这位大妈之后,继续赶路返回了连队。这也算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讨饭经历吧!
还有那么一次,不知道是哪一年。连队领导带我们一行5、6个人去山里背木头。当时心想是不是哪个领导搞特权,让我们为他们服务?后来才知道我们背的木头被用来盖了村上大队部了。
当时,进山买木头是要有计划的,朱阳有个木材管理站,凡是沒有计划的木头,从山里出来时,到朱阳以后被挡住是会被收缴的。不过,对农民而言,搭两间房子,用点木头,想搞点木材计划,连门都找不着,简直比登天还难!
若是听说哪个人搞了点木材计划,那么这个人是相当的有能耐了。当时盖大队部,沒有木材计划,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是否木材计划被挪用了?我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没有木材计划,连队一位领导带我们进了朱阳前面的一道沟,当木头出山时,不会经过木材管理站,当然也就不会被收缴了。
进了沟,走了有好几十里路,到了沟的尽头的一个村子,这是一个再往里连独轮车都难以通行的地方。但是,这里还是沒有什么树木,所需要的木头必须从里面背出来才行。
我们一行从这里再进山,走了十几里羊肠小道,又走了几里沒有路的道,直接上到了山上,这时才看见被山里人放倒的木头都倒在山坡密林里。我们便把这些木头拖下来,一步一步往山下挪。
说是木头,其实就是刚砍下的树,削光了树枝,连皮都未拔下。一根死沉死沉的,足有百八十斤。就这每人备好了两根,先从沒有路的地方,一步一个脚窝,小心翼翼的跨过脚下的小水流,把它先拖到有了羊肠小道的地方,再把这两根木头一根一根轮换着往前背。当到了急拐弯的地方,还需要把木头直立起来才能转过弯子。这么重的刚砍下不久的树,压在肩上,好疼好疼,要走十多里的羊肠小道,真的不是很好受!
就这样,把木头从里面背出来,寄放在村子里一户人家的院子中,继续再次返回山中。不知背了几天,最后终于结束了。木头放在山民的院子中,待慢慢晾干后,才能拉运。这下,总算是可以返回了。
后来回到村上,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走到大队部房子后面时,就想起了当时背木头的情景,真是太艰难了!
说是时间到了1981年,窄口的水进入了灵宝的西塬地区,终于实现了涧河水润西塬的梦想。不过这与我的家乡还相距甚远,也不曾受益。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家乡,到外地求学了。
作者简介:郭齐升,河南省灵宝市西阎乡谭建庄人,大学毕业后在兰州交通大学任教,退休后定居兰州。2020年9月回灵宝期间专程来到窄口水库,重温那段艰苦奋战感天动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