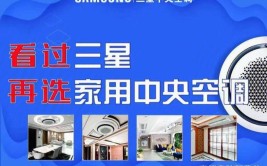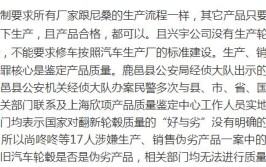原标题《某地一边打假涡阳,一边造假老子故里》
前言:“涡阳县天静宫只是老子母亲“感星孕圣”所妊之地——即老子母亲的娘家,是祭拜老子母亲的场所。”这是2019年某区针对涡阳县造假老子故里,以政府正式文件向XX市政府提出要“拨乱反正”的原句。
文件同时指出,老子故里——汉老子祠实则在“我区牛集镇姬揣李村等”云云。至此,“谯城老子故里说”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出现。

众所周知,涡阳县和某区同属XX市,如此明目张胆的互撕窝里斗,从侧面说明利益之下的争斗早已超出了学术研究范畴。所以,“谯城说”同时碰瓷鹿邑,人们并不感到意外。
只不过,人家涡阳赖好还有个与老子文化粘点边的“流星园”,“谯城说”实在拿不出手啥东西,于是就脑洞大开,先后找了几个认为是老子生地——老子祠(庙)的地方自认为故里,注意,他们是一个不行再找一个的指认,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此举又是如何的荒谬。
但不管别人怎么认为,“谯城说”为达其目的,还是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了一堆天马行空的所谓“证据”。但这些在专家看来,纯粹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信口开河、荒诞不经的言论,甚至连当地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的“考证”,实在是不值一驳(驳了又可能无形助其上热度)。
但考虑到长此以往,可能会对普通群众产生的迷惑性和危害性,两害相权不得不评析一二。
嘉靖《亳州志》
一、亳州史志记载的有关老子文化遗迹乾隆五年《亳州志·卷二·疆域志下·寺观》云:“自萧梁好佛,李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而寺观之建遍天下焉。亳为老子生土,其祀老子固宜,其宫殿之旧著名者例入古迹,合之为宫为观,亦寥寥无几。”证明至清代谯县境内的纪念老子的宫庙依然很少,见于旧地志的仅有亳州城内的道德中宫。
乾隆五年《亳州志·卷二·疆域志下·寺观》所云“老子祠在城东北角,万历间知州马成龙创著经堂,石刻道德经,建春登台于其左”即此。
明代的《寰宇通志•卷八十三•中都》在“寺观”条下所云“老子祠,在亳县,老子所生之地,后人立祠祀之,汉桓帝尝命边韶为文,久废”也应是指这个老子庙,但其明显把亳州城内的道德中宫与鹿邑境内的老子祠(太清宫)混为一谈。
近两年,当地个别好事者受利益驱使,为搏名出位,先后抛出与老子生地老子庙(太清宫)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三圣庙说”“姬揣李说”,那么,在“文物无证,国史无载,民间无传”的情况下,他们的脑洞又是怎么开的呢?
二、城内指鹿假“太清宫”三圣庙位于亳州老城北一里许、涡河北岸、小洪河之东,亳宋河之西。为了把老子生地圈定在亳州境内,“谯城说”感觉三圣庙与历史记载的老子生地位于“曲涡间”的地形有点相似,于是脑洞大开,计上心头,直接把宋代卫真县和老子出生地太清宫,向东平移到五六十里外的亳州城下——宣称三圣庙就是老子庙(太清宫)。
(一)篡改区划历史
亳州历史上虽在州府时期管辖过鹿邑(曹魏苦县、晋谷阳、唐真源、宋卫真、元鹿邑),但州府治所的谯城(县)与鹿邑的县界,一直泾渭分明,沿袭千年,从无更改。
元初之前,今鹿邑县名原为卫真县,县西五十里还有一座县城叫鹿邑县(县城治所在今鹿邑试量镇“鹿邑城”)。因遭受多年战争摧残和黄河水患,古鹿邑县人口剧减,于是元庭将西部鹿邑县撤消,并入东部的卫真县,取鹿邑县名,县治设在原卫真县城(即今天的鹿邑县城),史称“卫真入鹿邑”(去卫真县名,存鹿邑县名)或“鹿邑入卫真”(鹿邑县并入卫真县)。对比,《亳州志》记载的很清晰。
但是,“谯城说”为了辅证自己的意念想法,抛开《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等唐宋时期国家地理总志的确切记载,蒙骗不知详情的群众,公然篡改历史:愣是把史志记载的元初“卫真入鹿邑”,说成“卫真县西部合并入鹿邑,东部则合并入谯县”——按照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当时改名后的鹿邑县地盘只有自己治下的县城了。
历史架空剧也不带这样写的。
鹿邑历史区划位置《中国历史图集》
元初全国行政区划调整时,涉及的县很多,在“卫真入鹿邑”的同时,“城父入谯(县)”。元初谯县本来就是亳州所辖六县中最大的县,既然谯县东南70里的大县——城父县已经并入谯县,怎可能再把谯县之西的半个卫真县并入到谯县了。《元史》记载的“卫真入鹿邑”是整个卫真县全部并入了鹿邑县。亳州城在元代以前是州治所在,属郭下。而卫真县(真源县)在谯县西南部,西南最远已管辖到今郸城县宁平镇之南,元代以前卫真县无论如何也管辖不到亳州城的北郊。因此,亳州城北的三圣庙在古代既不可能隶属相县,也不可能隶属苦县,更不会隶属卫真县,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老子出生地的。
(二)编造子虚故事。
“谯城说”始建于明代的三圣庙,缘于元末亳州太清宫毁于战火,直接影响了亳州一带的道教祭祀活动,于是有人便在亳州城北就近修建了三圣庙填补这一空挡。但查有关史料,明代明令禁止私建寺观,也不允许为寺观改名;清代《亳州志》也均没有三圣庙的相关记载。因此,三圣庙很可能就是一近代产物,为使香火永世旺盛,才对外谎称是“老子出生地”。这就是三圣庙被现今亳州的有些道人口口相传为老子出生地的原因。
(三)生搬真宗行宫。
对了对应老子庙,“谯城说”又宣称亳州城内的道德中宫是古代的奉元宫(明道宫),可笑的是,按照这一说法,卫真县县界直接划到亳州城内了。
三圣庙、道德中宫位置及距离
史书记载的很清楚,宋真宗在赴真源县朝拜老子的第四天改真源为卫真县,其驻跸的行宫先叫奉元宫,后名明道宫(《宋史·卷一0四·志第五七》记载,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第二年到真源县后改为“明道宫”),位于卫真县城内东隅,东10里为太清宫。
明成化《河南总志》的记载:时鹿邑县治,就是元卫真县治
而宋真宗在亳州的行宫是“朝真回跸楼”,位于亳州西门外,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八月下诏始建。大中祥符六年(1014)正月二十三日,宋真宗在太清宫拜谒过老子后“发卫真县,次亳州,州城之西,设朝真回跸楼。
如此清晰的记载,“谯城说”却为了达其目的,肆无忌惮的让两个本属两地、相隔50里的行宫,硬生生的都捏在了亳州城内——把太清宫与明道宫的方位,由东西相望10里,变成了南北相对1里;更要命的是,如此以来卫真县的县城治所竟设在亳州城内了。
这种对历史的狂妄、对大众的蒙欺,可谓前无古人,惊世骇俗。
(四)硬套“灵溪”圣池。
为了证明老子故里在亳州城内,“谯城说”走把亳州城北的“亳宋河”指为老子生地标志之一的灵溪。
拜托,历史中的灵溪是“池”而不是小溪更不是河,把建国后才开挖的亳宋河,硬套在古代太清宫西南的灵溪池上(见上方”三圣庙图“),如此“信口开河”,感情大家在你们眼里都是大傻子么?
老子祠的位置史书早就说的很清楚,隋《老子碑记》(薛道衡撰)记载老子祠“对苦、相之两城,绕涡、谷之二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园;沃野平皋,东连谯国”。
这个“东连谯国”就是是说,隋代老子出生地位于苦、相县以东,亳州城以西,其间未隔其它州县。而三圣庙处在亳州城北,如此睁眼说瞎话实在匪夷所思。
二、麦田癔造伪“老子庙”
再看看“谯城说”相中的另一块“风水宝地”姬揣李村。该地位于亳州老城西约13公里、两河口以东。“谯城说”只所以在这一大片麦田上“选定”东汉老子庙,可谓颇费心机:
一是因为此地距离鹿邑很近——离鹿邑县界(也是省界)只有600余米,离鹿邑太清宫只有7.5公里,如此近的距离一般人很难搞的清。
二是那一带正好是涡河与惠济河的交汇处,就像他们“相中”的上一个“福地”三圣庙一样,这里与历史上老子生地的地理地势也有几分相似,值得大做文章。
可惜“谯城说”这一番的按图索骥注定又是一场空。
三地位置
(一)普通河湾指故里
1.该地自古就在谯县辖境,而历史记载的老子生地一直在秦汉苦县、唐真源、宋卫真、元鹿邑县境。而两河口东距亳州仅13公里,自古就在谯县辖境,从未隶属于苦、真源、卫真、鹿邑,那里怎么会有苦县老子庙或卫真太清宫?
鹿邑县界古今对照
2.其地虽然有涡河转弯处,但丝毫不具备大河湾的历史特征。史载东汉老子庙至李母庙南北之间里程约1000余米(崔玄山《濑乡记》曰: 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而这个转弯处的湾弧直径不足400米,南北不及两庙之间里程的五分之一,与《水经注》记载的赖乡城南和老子庙东侧的涡水长度明显不符,也无任何河流注入涡河,绝不可能是东汉王阜所说的“曲涡间”,更不可能是宋真宗所说的“涡曲神区”。
3.谷水湮灭已数百年,惠济河从来不是古谷水。两河口由惠济河入涡河行成,但惠济河绝不是《水经注》中的古谷水,因为古谷水在元初即已湮绝。
历史上惠济河的前身叫“黄河”,在元代才在鹿邑西通涡河,在清中期才经开挖于两河口处入涡河,河名还是乾隆亲自命名的。
清雍正时期,该地尚无惠济河
4.其地无任何文物遗址可对应,哪怕民间传说也无老子故事。地表上即无老子庙、李母坟、九龙井,也无灵溪池、古桧、石碑等任何与老子出生地有关的遗迹、遗址、遗物,随机访问当地上年纪村民亦无有关老子庙太清宫传说(近些年纠众新建的一个老子庙,也因自燃被一把火烧了)。
(二)乡野村庄造苦县
为了给自己的假设提供佐证,“谯城说”瞄上了本区牛集镇的安溜村(见上三地位置图)。该村位于两河口西北5公里,惠济河南岸,1949年之前隶属鹿邑,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乡村集镇,村中有棵古槐树,至今还流传着“一槐罩两省”的故事。
1947-1954鹿邑县境变化图
“谯城说”为了佐证老子祠,便嫁接史书中“苦县东十里有老子祠”的记载,愣是将安溜惠济河大堤指为“苦县古城遗址”。
另外,还把曾经的一个老庙“问里宫”,愣是说成孔子“问礼”处,实际是当地人根据“孔子问路老子家尚有几里”的一个传说而建的民间纪念物(现在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记得这个传说)。
安溜《问里宫》 石匾额
(三)无字砖瓦定结论
“谯城说”在地表上找不到一丝与老子庙相对应文物遗存的情况下,又开始打起了地下的主意,竟然用毫无价值的出土文物“证明”自己。
2018年4月,“谯城说”们游说谯城区政府,申请上级有关部门委托西安鼎诚勘探有限公司,对牛集镇姬揣李村,魏岗镇孟庄、高庄、三王营、谭楼老村旧址等大片区域进行了所谓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勘探到“跨越年代较长的汉——宋元时期的古遗址”。
至于具体是什么遗址,谁的遗址,考古结论没有交代,“谯城说”们却如获至宝,然后发文出书——把这些既无历史文献记载,又无相关铭文的所谓文物——砖瓦盆灌,公然认定其为老子故里老子庙。
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亳州古属河南所辖,在两河口东侧地下能挖出汉砖陶器并不意外,相反,别说在两河口,大凡在华夏大地都能挖出地下遗物,如果拿这些没有铭文碑刻的东西就认定为是老子故里,那全天下有秦砖汉瓦的地方岂不都是老子故里?
综合“谯城说”上述通篇荒诞不经、匪夷所思的“认定”和“证据”,不难看出其执拗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老子出生地或者在亳州城北的三圣庙,或者在亳州城西的两河口,或者在亳州城西北的安溜集,总之是在安徽省境内而不是在河南省辖境就行。
只是,这种以“卫真县管辖到谯城区”“涡水永不改道”“谷水永不湮绝”为假想前提,以“惠济河就是古谷水”为要件,以混篡改隐瞒历史为手段,意图打造出一个新的老子故里的操作,实在毁人三观,难以直视。
附:亳州(谯城)历史沿革亳州历史上虽在州府时期管辖过鹿邑(曹魏苦县、晋谷阳、唐真源、宋卫真、元明清鹿邑),但州府治所的谯城(县)与鹿邑县界一直泾渭分明,从无交织。
1、根据弘治《中都志》和康熙《凤阳府志•卷之第二•沿革》,亳州历史沿革如下:
《禹贡》豫州之域,商所都也。
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即此地。
春秋为陈国之焦邑,后属楚。
秦属砀郡。西汉为谯县,属沛郡。
东汉属沛国。魏置谯郡。
晋因之。北魏置南兖州。
后周改置亳州,兼置陈留郡,改谯县曰小黄。
隋初郡废,开皇十六年,分置梅城县,复为谯郡,寻改小黄为谯县,并梅城入焉。
唐初为谯州;武德四年,复为亳州;天宝元年,改亳郡;乾元元年,复为亳州,领谯城、父酂、临涣、鹿邑、真源、永城、蒙城八县,属河南道。
五代,梁为防御州。后唐为团练州。晋复为防御。
宋大中祥符七年,升为集庆军,属淮南路;熙宁五年,分属淮南东路入于金,为防御,隶南京路;贞祐三年,升集庆军。
元复为亳州,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以睢阳、永城属河南归德府,后复置城父州领之,而谯、城父、鹿邑三县隶归德府;至正十五年,伪宋僭都于此。
明洪武初,改州为亳县,与鹿邑县并隶河南开封府归德州,后改隶凤阳府,属于颍州;弘治九年,改县为州,仍隶凤阳府。
2、嘉靖《亳州志》。
该志前部分与以上记载基本相同,所不同之处在明初。嘉靖《亳州志》云:“国朝洪武初仍为亳州,谯废,隶河南开封府。六年改为县,隶凤阳府颍州,编户七里,城父亦废、并谯入于亳,鹿邑仍属归德州。弘治九年,巡抚李公蕙改亳县为州。”又云“国初亳属开封为州,次属颍州为县,次统于凤阳,旋复州治,均一地也”。
嘉靖《亳州志》认为明洪武六年之前仍为州,辖鹿邑县,隶属河南开封府。洪武六年才降为县,与鹿邑分道扬镳。而《中都志》和《凤阳府志》则认为明初就已经降为县,与鹿邑县同属河南归德州辖。明成化《河南总志》、嘉靖《河南通志》、嘉靖《归德府志》也云国初归德州就辖鹿邑县。
由此可见,谯县自古就未管辖苦县(卫真县),两县也从未曾合并,两县之间界限分明。清光绪《亳州志·卷一·疆域》也有按语曰“志云,今亳州实得汉三县之地,谓谯及城父扶阳三县也。”可证谯县至清末仍未辖有古苦县之地。
3、建国以来。
从鹿邑、亳州旧志所载两县地图也可以看出,元明时期,鹿邑与亳州(县)的分界线在安溜、怀溜、郑集一线,两河口及以东地区隶属亳州(县)。两县之间界限分明,甚至连插花地也不曾存在。而鹿邑与临近的柘城、淮阳在清代仍然有插花地存在。
1949年,鹿邑、亳州(县)行政区划进行微调。涡河以北安溜、戴桥等村由鹿邑划于亳县,涡河以南怀溜、叶庄等村由亳县拨给鹿邑,但赖乡太清宫始终在鹿邑辖境。
1986年,亳县撤县设市。2000年,***批准设立地级亳州市,原县级亳州市辖境新设谯城区,辖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