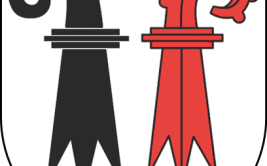桓台县:康杨村
康杨村位于县城西北 21 公里处。旧村东西长 450 米,南北宽 440 米。村内有南北主街 3 条、东西街 2 条。新建成的康杨生活区东西长 300 米,南北宽 260 米。区内有东西主街 1 条、南北主街 1 条。村北靠西孙村,东北临马桥村,南临小庄村,西临北营二村、北营一村,南一环路从村南东西走向穿过,连村路小康路从村中南北方向穿过,北距镇主干道红辛路 50 米。
全村现有居民 393 户、1343 人。现有耕地 1110.57 亩,人均 0.827 亩。

康杨村原由 2 个自然村组成,南有杨家庄,北有康家庄,两村之间原隔一座土崖。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分称杨家庄、康家庄,光绪三十年(1904)合称杨家庄,1933 年更名康杨村。
明朝初年,康杨村杨氏谱宗杨嗣田兄弟三人自直隶枣强县迁鲁中。按照明朝廷的规定,兄弟不可同住一村,因此兄弟三人中,一个定居高青县青城镇;杨嗣田定居新城县北乡,新立杨家庄;另外一人则去了淄川县。由于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三兄弟失联。杨嗣田立村后,子孙后代日子过得贫苦。传到八世,族中仍没有一个读书人。世系传承制谱修牒之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族系资料尽皆散失。杨氏盛世修谱时,只得从十世下修,定杨嗣田为谱宗。令人欣慰的是,在修谱中,杨姓人找到当年别居的另外两兄弟的后裔。640 余年来,失散的杨氏一家人的后裔终于得以团聚。
康刘一家
明朝初年,康姓人家迁此立村,取村名康家庄。后来,康姓人在村北修了一座浆水庙(又称七神庙)。由于庙宇修得庄严宏伟而遐迩闻名,被周边村庄称为康家庙子。
康姓人立村后,又有琅琊刘氏从诸城迁来定居。两姓居民和睦相处,共建家园,礼尚往来,世有联姻之谊。清朝光绪年间,新城西北乡一带常闹水灾。特别是孝妇河更是十年九涝,水患频仍。孝妇河西自长山县流入新城县。因为洪涝连年,两县居民时常发生争端以致械斗,自然灾害再加上人祸,使这里的居民受尽了苦难。康家庄虽不靠孝妇河,但离两县发生争端和械斗的地方也有 10 多里。每至汛期,新城县的地方政权常征地方民伕参加防汛。这样一来,康家庄的民伕就常被派到孝妇河两县交界处值守。
这年盛夏,孝妇河水势汹汹,两县民伕在地方官吏的唆使下持铁锹、木棍欲斗。康家庄的康大枪、康二枪(民间传此名,疑为绰号)兄弟俩,看到对方蛮不讲理,欲扒堰放水涝新城县的土地(这一段地势西高东低,扒堰即东流),即挥锹冲向对方。
械斗中,康大枪兄弟失手打死了长山县的人。翌日,长山县衙告到济南府,济南府命新城(即桓台)县衙到康家庄捉拿康大枪兄弟二人抵命。在地方乡绅的斡旋谋划下,康家兄弟连夜外逃。康姓所有人众全部投靠同村刘姓姻亲,更姓为刘。新城县衙到康家庄拿人时,闻听凶手在逃,康姓人家也都“逃跑避祸”,村中只有刘姓人家,遂据实上报,了结了官司。从此,康家庄的康姓人姓了刘,这就是康杨村康刘一家的由来。
虽然康大枪兄弟漂泊在外,没了音信,但大枪兄弟舍命护乡里,康家人众避祸改姓刘,却在马桥一带世世代代流传。曾远近闻名的康家庙子直到 1985 年以后才全部扒掉。
杨家楼
杨家楼是一片墓田的名字,坐落在康杨旧村西 800 米外的田野中,占地 21.97 亩,具有 600 余年的历史,是马桥镇诸村最大的墓田,因此闻名于周边村庄。现在,墓田中尚有一块石碑,碑文介绍了这片墓地的长、宽和占地面积。
杨家楼墓地是康杨村杨氏一族的坟茔。据杨氏宗人介绍,谱宗杨嗣田到此立村后,即建此族内公茔。640 余年来,杨氏族人亡故,都葬于此茔中,从未另辟坟地。这在桓台县也是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杨家楼墓田中栽有松柏 500 余株,其中树龄超 500 年的古松有 50 余株。1956 年,地方政府修木辛闸时,伐掉墓田中的松树修了木辛闸带桥。
据说,杨家楼墓田中还种有大杨树,最大的胸径在 1.8 米以上。1939 年,日本侵略军修岔河炮楼时,把墓田中的大杨树强行砍伐。现已年届 83 岁的村民杨某说,伐大杨树时,他已经 6 岁,曾到伐树现场。伐倒的杨树树干两边站人,谁也看不到谁。硕大的树干,用 6 对铁瓦车脚才运到岔河去。
杨楼墓田中到处长满黄蓓草。这种草能长 1.6 米高,秋天割掉可以喂牲口,明春又能生长出新芽。每到夏秋,杨家楼墓田,苍松森森,碧草深深,形成一道特有的景观。
大墓田中,野生动物很多,如狐狸、貔子、獾、野兔、刺猬等。原来这些野兽常遭猎人捕杀,但到了抗日时期,日本侵略军在附近炮楼(北营炮楼、陈庄炮楼)听到枪声往往倾巢出动,寻找打枪地点,途中沿路祸害乡民,因此在这一时期,猎人不敢放土枪打猎,墓田里的野兽经繁衍多起来。墓田内食物不足,附近村庄的鸡、鸭等便常常遭到狐狸的侵害,狐狸抓鸡的事情在夜间经常发生。杨楼墓田里的狐狸大如狗,其中有些狐狸非常狡猾。有的能学人语,人称话貔子;有的能玩萤火,人称火貔子。本地有许多关于貔子的传说。
传说,墓田中的貔子成了精,脱化为人形到北京郎家胡同做买卖。老貔子回想起住墓田时,老貔子住下层的坟砖槽子,小貔子住坟顶部的土洞,这不就是住的楼吗?因此,老貔子给老家的貔子写信时,把收信地址写成了“杨家楼”。信邮到老家后,费尽周折才找到。从那时,这座墓田便有了杨家楼的名字。
其实,这个传说是很荒唐的。我国的邮政开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当时称大清邮政,由英国人 S. 赫德任总邮政司。极有可能是国内通邮后,在北京做买卖的康杨人给家里写信时误把“杨家庄”写成了“杨家楼”,而村人又以此作为这片墓田的名称。
日本兵火烧康杨村油坊
1940 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日军中队长松田率焦桥据点的鬼子到康杨村“扫荡”。他们听说康杨油坊里夜间曾住过抗日部队,就疯狂地将油坊放火。30 余间房子全被烧为灰烬,房内的 6 大缸豆油(3000 余斤)以及所有榨油设备全被烧光。在此看家的村民张光永被打烂嘴巴,油坊的合伙业主倾家荡产。
袁家坟的传说
康杨村原有一座古墓,坐落在康杨村南、现在的南一环路与小康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古墓地占地 2000 余平方米,主坟高 5 米,本地人称其为袁家茔。茔中有 2 座大 坟,一为袁家小夫人坟,另一为小夫人之大儿子坟。茔中原有巨碑,于解放初拆碑运黄河作防汛物料用,碑上文字失录无考。2 座大坟于 1955 年初冬被扒,后来被取土拉平。茔地南侧现在建了养鸡场,东侧建设居民二层楼,其余是农田。
当时,社会上平坟垦地的风已经刮起,这是因为当时农田中墓田太多,多则几十亩, 少则几亩。有的村墓田面积已占到村耕地面积十分之一以上,田中出现“一村十八姓,三十六坟茔”的情况。
平坟扒砖是从 1952 年开始的。解放初期,分田分地后的农民革命热情非常高涨。政府号召兴修水利,打井灌田,架桥铺路。做这些事需要物料,政府号召把墓田中的石碑、石供桌用来建桥或防汛,于是各村拆碑建桥蔚然成风。此后又提出“老社员献地”“老社员投资”“老社员献砖”的口号。到了 1955 年,农田打井形成高潮,但一穷二白的农业社缺少垒井的砖,于是扒坟拆砖成为垒井用砖的来源。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康杨五星(五)农业合作社组织人手扒了袁家茔。
首先扒开了大坟,硕大的墓室中放一个涂了枣红漆的楠木棺材。棺材封闭非常牢固。众社员用铁钎、大锤、洋镐,费尽气力才打开了棺盖。抬下棺盖后,棺内女尸面容栩栩如生,身穿绸缎彩衣,头戴金冠冕,似乎慢慢从棺材中坐了起来。众人吓得一哄而散。独有大胆二愣子无所畏惧,上前摘下女尸头上的金冠冕,撸下女尸双手上的金镯子,并搜尽棺内的金银玉器、首饰器皿,一并交于墓上的负责人。说来也怪,在搜拿宝物期间,女尸的绸缎衣服就逐渐残破,女尸面容也变成灰土色。人们赶紧先把女尸埋掉,再清理墓中器物。
小坟中埋着 3 具尸体,一男二女。这三具棺材质量就差了,棺中已进水,尸体已变成了白骨。3 具尸体双手都佩戴金镯子,还有其他首饰。据人们揣测,大坟内尸体保护完好,主要是因为棺材密封得好。除通体涂有树胶黄香外,还多遍上漆。开棺后,看到漆层有煎饼那么厚,由此可见墓中女主人生前地位显赫。
民间传说,袁家的坟茔在焦桥,而这片墓地原属小庄村,在土改中才划给了康杨村。也就是说,这座小庄村的袁家茔是焦桥袁家大坟茔之外的外庄园。只有不能入祖茔而又地位显赫的人才会葬在这样的地方。
传说,墓中女主人是大老爷的小妾。这位小妾原是袁家的烧火丫头,长到长发及腰时被大老爷看中了,于是被秘密收房。但大夫人是个醋坛子,规定小妾没有名分,照旧烧火做饭,并且生育儿女后,立即抱给大夫人护养。谁知小夫人一连生下 4 个儿子,个个英俊聪明。长大后,有 3 个儿子考中秀才,其中一个又考中了举人。孩子们大了,一直认为是大夫人所生,但族中有人暗暗把原情告诉了他们。孩子们与生母秘密相认后,小夫人为孩子们设了一计。时值炎炎夏日的中午,4 个儿子都穿上棉衣在大厅前晒太阳。大老爷和大夫人看了感觉奇怪,就问他们:“大热天穿棉衣晒太阳,你们不热吗?”孩子们回答:“我们热, 那么烧火做饭的就更热了。”一句话戳到了大老爷的痛处。于是,大老爷力排众议,给了小妾以小夫人的名分。小妾由此从下人变成半截主子。
名分改变后,小夫人就可以与 4 个儿子朝夕相处了。她虽然不识多少字,但天性聪颖,督子读书格外勤苦。孩子们也学业大进。不多年,有 2 个儿子参加殿试考中进士,另 2 个儿子考中了举人。但是,这时候,大夫人生的唯一一个儿子虽年近不惑,犹未有功名,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大公子去问小娘:“叩问夫人,不知我如何才能考中呢?” 小夫人沉吟不语。大公子只得连连叩首,长跪不起。过了一会儿,小夫人说:“孩子呀,若想考中,除非为娘我再生你一次!
”大公子听了,再叩首说:“愿听娘安排!
”于是, 小妇人命人做了一个特大裤子,穿在自己身上。又叫大公子入裤后,再从裤腿中钻出。这时,小夫人说:“这样一来,你就是为娘所生了。”
说来也怪,从此大公子学业有进,竟考中秀才。自此,大公子把小妇人尊为亲娘,朝夕伺于膝下。后来,小夫人辞世,按祖规不能入祖茔 ,大公子申请,愿陪小夫人,死后葬在小夫人之侧。
坟中的女主人就是袁家大老爷的小妾,坟中的一男二女就是大公子和他的妻和妾。小夫人辞世后,按袁家祖规,不能入祖茔。但那时小夫人的 4 个儿子都已做官为绅。
母以子贵,小夫人也应得到应有的礼遇。于是,袁府众议,将位于桓台县境内的小庄庄园拨予小夫人,另立袁家茔。在丧葬仪程中,大夫人(小夫人去世早)坚持棺材不能从袁家大门出,必须从便门抬出。理由是不是明媒正娶的夫人,死后必须从便门出丧。
这个意见,小夫人的儿子们不同意。大夫人生气地说:“你娘们势力大了,从天上走吧!
” 一句话给小夫人的孩子们以启发,于是从府内扎制天桥。天桥从大门顶上通到府外,小夫人的棺材就通过天桥抬出来。
小夫人出殡,彩棚一直从焦桥扎到康杨墓地,有 10 多里路长,让小夫人的棺材行不见天。出殡之日,出天桥,过彩棚,鞭炮相闻,唢呐笙簧悦耳,好一派风光景象。小夫人的冠冕系纯金打制,重约 1 市斤;手镯每只重 4 两(过去的小两),2 只重半市斤。大公子和妻妾的手镯也是每只 4 两重。这样,连其他首饰器皿共有金器 4 市斤 5 两,还有 1 枚金蝈蝈、1 座瓷牺尊和其他玉器。当时,收集宝物均在众目睽睽之下。收集完毕之后,由 2 名负责人携带宝物,并派民兵随行保护送到陈庄区公所。由区机关开具了收条并盖上印章,此收条至今还在康杨村财务档案资料中。此后,政府奖励五星(五)农业合作社 650 元人民币(那时币值很高)。康杨村用这部分资金买了一部胶轮马车,买了 2 匹马,壮大了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力。(桓台政协文史委)
【本文选自淄博政协 特此感谢原作者】